
真是如此之和平浪漫吗?那些欧洲来的入侵者仅仅以拳头对付印第安人的长矛?眼前的轻歌曼舞毫不迟疑地掩饰著当年的腥风血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先后殖民阿根廷。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拉博卡登陆不久,就深入彭巴斯草原。在那里,这些人重操旧业,务农放牧打猎,后来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高卓人’。直到1930年代,高卓猎人仍以印第安人的头颅领取奖赏。殖民者将原住民赶尽杀绝,如今只有巴拉圭边界遗留少数瓜拉尼人,而火地岛人和阿拉帕契人都早已绝种。阿根廷的欧洲移民无比热爱这片土地,然而,他们也以霸主的姿态消灭了所有比他们先到此地的人们。圆形舞台晶莹剔透,手风琴激昂、提琴婉转、钢琴明朗,一听就是探戈的2/4节拍的音乐。女人一袭鲜红长裙,鞋跟细高,大开叉下玉腿若隐若现。男人身著深色西服,油亮的大背头一丝不乱。他站在女人背后,手抚女子肩膀,随乐声快速向后甩腿。
女人转身,以仇恨的眼神盯视男子,却又将手臂扬起。在男人的引导下,二人一掌相握,一臂互拥,蟹行猫步。前进后退侧行,移动交错缠绕。拧头出手转身,干净利索,带有一种军事化的坚定不移。舞者的上半身直立不动,表情冷酷,全无摆荡,而两腿却缠斗激烈,快速而复杂。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上半身道貌岸然,而下半身放荡不羁。这上下半身的动静错落,兴奋的音乐和冷静的舞蹈,燃起一种压抑著的激情。
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布市的移民聚集区域,拉博卡一带的港口河岸,滞留著大量的船员以及各国移民。这些人形成特殊的外来社会群体,咖啡馆、夜总会和酒吧应运而生。生活贫困的人们在酒吧里靠酗酒、唱歌、跳舞来消磨时光或发泄郁闷。哈巴涅拉、波尔卡、西班牙的对列舞,非洲的坎多巴在此交汇混合,更因注入阿根廷牛仔高卓人的马背音乐米隆加(Milonga),熔炼成探戈音乐和舞蹈。虽说探戈的舞蹈语汇是从拉美、欧洲和非洲的民间舞蹈演绎而成,而双腿的快闪急动,却是模仿布市贫民区械斗时的刀光剑影。
音乐自热烈转入轻缓,灯光熄灭,舞台若夜幕下的某个时刻。白日喧嚣之后,提琴如泣如诉,舞者在一束追光下缠绵。他们握持紧密,四目相对,并行直立,身体几乎贴在一起。夜色深沉,似乎天地之间只有这对男女,也似乎因为只有这对男女,孤绝的味道渐浓。孤立隔绝之中的男女,逐渐不耐,烦燥不安。男子侧身引导,女人适时回应,倒步旋转带出力道,于是波澜又兴,争斗再起,舞者双腿穿梭如疾风闪电。往返交织,层层逼近,完美的断音,骤然停止,定格--女人伸出玉腿,缠绕男人腰间。
在阿根廷,探戈是一种唱多于跳的艺术形式,非常不同于社交舞和国际标准舞中的探戈表演。早年的探戈唱词融入许多黑社会的切口暗语,监狱中的俚语粗话,即使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也未必全能听懂,这也许是造成世界对探戈误解的原因之一。或许由于无法解读歌词,外人就将注意力转向形体动作。好莱坞的影片将探戈漫画化,也为误解探戈推波助澜。未到阿根廷之前,我亦有同样的误解。
今晚,在这间名为老仓库(El Viejo Almacen)的剧院里,我第一次体会到音乐是探戈的灵魂。这一场探戈表演,除却舞蹈,独唱、二重奏、合奏、插科打诨穿插其间。探戈歌手多为男性,正如舞台上的那位男中音。他声情并茂地唱著,虽听不懂唱词,但那显然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观众如痴如醉,以掌声相随。音乐表达著迷思与渴望,恰如来自彭巴斯草原的狂风,银河上的大潮。
作为移民文化的产物,探戈音乐必是忧郁怀旧思乡的,唱词又多以失恋的故事表达诸多的伤感。失恋大约和早期移民男女比例过于悬殊有关,听说男人要时刻提防周遭四在的情敌或仇敌,故在探戈舞中,时刻拧头而无暇与情人对视。翻捡那些译文唱词,大多是失去女人,渴望母爱,混杂著爱恋、温柔和赞美、厌烦、轻蔑与仇恨。在被女人所抛弃的悲伤之中,潜流著强烈的恋母情结,因为只有母亲永远无私地奉献,恒久地接纳和理解。
多情自古伤别离。然而,当人们表达离情别恨时,东西方却又是那样地不同。中国人多寄情于诗词,西方人多借助于音乐舞蹈。晓风残月,断雁无凭都成为中国诗词中的托情之物,其中之含蓄凝炼,令人把玩咀嚼。西人在诉说羁旅之无助与无奈的同时,更容易沉缅于失恋的痛苦,又多以节奏强烈的歌舞来发泄其忧愤。这个中之差异,犹如东方的武侠传奇和西方的骑士文学。
舞台上出现了一组男舞手,黑西服黑礼帽,跳起来颇似三四十年代电影中的特工。女特务随后登场。五个女人穿著五种颜色的西服,戴著同一款式礼帽和领带,登著同样颜色的高跟鞋。下身似乎只穿长统丝袜,只有当她们举臂时,那同色的短裤才若隐若现,顿时口哨尖叫四起。在阿根廷,探戈不仅展示一种品味,更是证明男性力量的仪式。表面上,似乎男女舞者不分轩轾,甚至更突出于女人的娇冶风情,然而这暗中的推手确实是男人,无人置疑探戈的阳刚。
1992年出品的《女人香》是好莱坞少有的几出探戈正剧。艾尔帕西诺饰演的退役中校双目失明,完全凭音乐的感觉以及捻熟的舞技,带起从未跳过探戈的女人,跳了一场堪称经典的探戈。电影中那段探戈音乐的名字就叫《女人香》,其作曲者为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la)。上世纪中期,班都尼昂小手风琴手、作曲家皮亚佐拉探索探戈与爵士乐之近似,并成功地将这两者融合,创造出展示即兴和随意的诺瓦探戈。在探戈的音乐世界里,皮亚佐拉的地位犹如爵士乐中的杜克埃林顿。
诺瓦探戈的舞者擅长于利用音乐,譬如断音的表现、突起的动作、戏剧性的停止,通过音乐的特别效果来演绎随意和即兴。犹如聆听爵士乐,观众永远不知道舞者下一步的动作,他的女舞伴也不知道。许多知名的探戈舞大师甚至也承认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将要做什么,然而对于音乐的捻熟和诠释,长期合作培养起的如呼吸般的协调,只要男性舞者一个暗示,女性则自发地跟从。于是,男舞手不仅为观众带来意外,也令其舞伴惊喜。
待‘特务’们下场,舞台转出五位手风琴手,每人的膝上都垫著一块方巾。如果说探戈音乐是舞蹈的灵魂,那么探戈乐队的灵魂就是手风琴。在古钢琴、吉他、中小提琴和长笛中间,手风琴往往最为活跃,最引人注目。此时一排五位琴手,真不知他们如何一争高下。音乐如军队行进,风琴也踏步式地抖动。跌宕起伏,高潮来临,五座风箱开闭如扇。曲罢,掌声雷动。五位风琴手的正中是一位白发老人,他显出‘还不算太坏’的表情。
乐声再度响起,自头几个音符,我就听出那是‘别为我泪盈盈,阿根廷’。在此地,音乐剧‘埃维塔’并非人人喜爱,但这首由美国人创作的歌曲却道出阿根廷人的心声。安卓韦伯的曲子隐含哀怨,非常动人。我们的导游曾说,一听此歌她就热泪盈眶,特别是近年,阿根廷经济遭遇重创,引发社会动荡,聆听此曲更添几分悲壮。此时全体探戈舞手都已登台,跳得庄严肃穆。一幅巨型阿根廷国旗自高处哗然落下,五对舞者各持国旗一角,整个表演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中结束。
步出表演厅,已近夜里10时,而布市似乎刚刚饮过它的‘Early evening cocktail’,如孔雀般地展露它艳丽的屏羽。我们入住的旅馆位于知名的佛罗里达步行街附近。这条街两旁店铺林立,热闹非凡。许多饭馆酒吧咖啡店都通宵营业,食客出入犹如午间。最引入注目的是那家名为‘牧场’的烤肉店。落地玻璃窗前,一只只肥猪被撑开,围炉而烤。满店人头攒动,随处可见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夜色深沉,人流依然涌动。街头艺术家犹如旋涡,吹拉弹唱,泛出圈圈涟漪,街头随意辟出的探戈舞场卷入最多的观众。在这里,探戈不仅是声音、形象,甚至是一种气味,和城市的潮气一样无时不在,沁人肺脾。
一处探戈舞场的中央站著一女一男,他们邀观众共舞,顺便赚点儿小钱。既然是有偿共舞,自然都是有备而来,且舞技不俗。一位显然是游客的先生自动请缨。那是一位年过古稀的小老头,看来身板不错,不过毕竟已是高年,能带得起那20来岁的女子吗?一捱音乐响起,那老者镇定自若,沉稳有力。女子被带著满场飞动,轻击快转,华贵雍容。手风琴的切分音敲击著两个素未谋面之人的心,默契为旋律所滋养,绽开随意和即兴的花朵。这一对舞伴越舞越劲,一忽儿嘻戏明快,一忽儿深情忧郁,快速旋转的疾风掀起女人的披巾,速率一致的波浪诱得男人心摇神旌。舞罢,老人脸色红润,拥著老妻,兴致勃勃边走边说,似乎在回味其当年之勇,认为刚才的表演也不过尔尔。
数年前,在一次月夜滑雪中,曾与一位居住布市多年的医生相遇。他对布市的评价真是入木三分。他说如果你想访问历史古迹,如果在此城的某一角落迷失,你必感到乏味,因为那里确实没什么可看的。最有趣的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坐在咖啡馆里,从薄暮直到天明,你必能从不同的人那里,听到许多稀奇的故事。如果你想体验彭巴斯草原的空旷,或者观赏伊瓜苏瀑布的妩媚,或者领略佩里托莫雷诺冰川的壮丽,你必得向北或向南再行几千公里。然而,若想看俊男美女,想欣赏探戈,即在布市,你便能如愿。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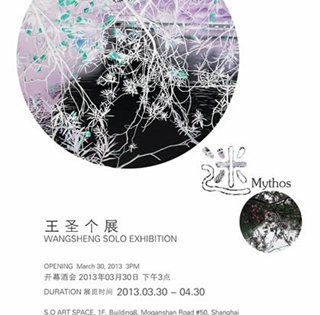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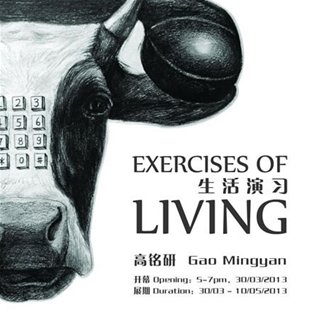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幽雅的旋
幽雅的旋 西班牙—
西班牙— 恰恰恰,
恰恰恰, 秋天 到巴
秋天 到巴 巴西:火辣
巴西:火辣 爵士舞-燃
爵士舞-燃 扭秧歌
扭秧歌 保安族的
保安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