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往摄影家的意识中,摄影主要是作为记录客体的一种媒介手段而存在的,比如常见的生活摄影、新闻摄影及艺术摄影。当然,所谓艺术摄影是强调审美的,一件摄影作品除了题材、技术作为衡量一件作品优劣两要素外,所谓的意境美感构筑着一件摄影作品品位层次的高低。尽管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高度发达的网络资讯时代,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社会结构与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变化,但摄影界仍稳如泰山,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贯的创作原则,在从"摄"到"影"的流水生产线上不断制造出大量雷同的旨在发表、获奖的平庸之作。这些"美"、媚俗的摄影作品大都是出自那些操持国家相机的拒绝思想的摄影家之手,既毫无新意,又无任何观念上的改变。近十几年来,与当代文学、电影、戏剧以及艺术界相比,摄影界虽然也出现了个别有思想的"异端",但总地来说,仍是一片"春风不渡"的艺术荒漠。所以,观念摄影没有首先出现在摄影界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到了一个不断实验、蝉变、发展的新境地。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更多的当代艺术家摈弃了带有农业社会手工文化色彩的架上绘画加入到媒体实验的行列。装置、行为、影象等混合媒介技术的应用已然成为前卫艺术家习以为常的表达形式。在此情境中,摄影这种原本在艺术家的应用范围中只作为记录过程与结果的辅助性媒介,在新观念以及当代电子文化的激发下,悄然转化为可直接完成艺术家观念设想的重要表现方式,由从属的手段--副产品转变为呈现观念的主体,即作品本身。摄影这种从"手段"到"目的"(作品)的转变是意味着摄影作为艺术在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化--摄影从此具有了不同以往的观念诉求。在这种观念化的摄影作品中,摄影的审美功能理所当然地让位于作品的观念思想的表达,摄影由人人信手为之的"照相"抽身蝉变为前卫艺术家从事精神创作活动的新媒介,进而使摄影由视网膜的艺术上升为思想的艺术,并在中国前卫艺术实验媒材变革中显示出日益强大的力量。
从具体创作的角度,观念摄影并非象一些滥竽充数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人人可顺手操弄的把戏,事实上它虽然并不刻意要求艺术家自己操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一些艺术家的摄影作品是请人拍摄的),但却特别要求艺术家要具备良好的反省现存文化的思维能力。一幅好的观念摄影作品并不意味着通过高技术指标呈现其所摄对象,符合美的形式原则,重要的则是要通过图像有力的表达出艺术家主体独异的精神观念。近年来,对这种新影象艺术--观念摄影的研究和批评刚刚开始,批评家和艺术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之命名:"新影象"、"新摄影"、"新概念摄影"、"观念摄影"等等。在这些命名中,"观念摄影"似乎更为约定俗成,也更为从事影像创作的艺术家认同。然而,从事影像创作并非意味着一种职业化身份确认,事实上,摄影仅仅与大多数当代艺术家所从事的行为、装置等观念艺术的创作活动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但正是在这种联系的发展中,摄影的地位才变得愈来愈重要起来的,以至于发展为具有独立品性的观念摄影。而观念摄影仅仅是一种表达观念的媒介形式,并非采用这种方式就先在的具有某种优越性,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艺术家是否真正创作出了好的作品。一件可以称为"观念摄影"的作品应当不仅仅只是一个行为一件装置的摄影记录,或是牵强附会地通过文字阐释解读才能让人知道其观念所在,而要求图像自身就应具有可辩识的观念性及其自在价值。确切地说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其一、图像具有可识别的独异的观念性。其二、观念的表达必须建立在强烈的视觉语言之上并具备能指与所指的逻辑自足性。
在一系列名为《异地看电影》的照片中,主要人物是两个头带面具的怪客,背景通常是一处街景,也可能是一处空空荡荡的影院,或者是刚刚开动的公共汽车……怪客周围的人脸上现出莫名的惊恐和紧张,有的似乎正在窃窃私语......这是成都艺术家戴光郁与刘成英1999年在四川实施的行为《异地看电影》中所呈现的情景。面对这些连续的摄影图像,如果我们仅仅将此视为一个行为过程的副产品,想象行为者已经终结了的行为过程,我们必然会丧失感受该系列图像本身通过特定的视角所传递出来的观念信息: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面孔已然被各种各样的诱惑与忧患所蒙蔽,人的自然本性已经丧失殆尽。在一个只有习惯于假模假样才能安身立命的虚伪的社会规范中,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冷漠而麻木的,以至于每个人不得不在相互交往中带上一副可笑的虚假的面具。虚假的面具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需要、一种现代生活必需品、一种无师自通的社会本能。图像中这种貌似荒诞的行为显露出的却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真实而尴尬的面目。当我们对两个突然闯入者激起的尴尬情景忍俊不住开怀一笑之后会惊诧地发现:两个行色匆匆的怪客脸上的面具正在我们自己的脸上隐而不露地戴着;他们那些夸张、机械的防范动作不也正表现出我们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心理状态吗?与戴、刘相似视角的是王国锋的影象新作,后者同样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街景。然而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王国锋没有采取戴光郁、刘成英式的行为化表演,而是保持了一种身在其中心在其外的冷静,他将在街上拍摄回的样片象一个侦探一样放在电脑中逐一甄别--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忙忙碌碌的我们只不过是些行色匆忙的过客,一些在时间中转瞬即逝的影子,而且这些影子被"机器"操纵着的。在这里,"机器"既指操纵图像的电脑,也指操纵人的行为规范以及思想的国家机器。画面中,后者的代码--带大盖帽的警察正闪回在人群中--这个发现经过王国锋的镜头进入电脑程序并以马赛克化处理加以提示,然后进入我们的视线。在王国锋看来,在某些情境下它们两者在执行命令时具有某种相同的性质和作用:为所欲为,保持秩序。由于借助了电脑丰富的数码操作功能--复制、移位、虚化及马赛克等多种变幻形象的语汇,在题为《记录-f8,1/125》系列画面中呈现出流动、变异、形象破碎与主题不确定等后现代征候。它在解构我们社会化的视网膜经验与被驯化的思想观念的同时,巧妙地揭示出暗藏于我们身边的恐怖以及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被支配被规定的生存处境。
周啸虎近期的影象作品一直在对人的面部做一种近乎心理医生或外科手术般冷酷地分析处理和甄别。在这些作品中,一个个道貌岸然的熟悉的形象在艺术家的审视下被无情地撕去伪装,然后,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定格的画面中,一张脸紧挨着一张脸,一个形象渐变为另一个形象--这些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主宰、偶像、明星或大师的人物,他们曾长久地占据着我们的意识,使得我们无可奈何地丧失了思想,甚至丧失了作为个体存在的理由。在周啸虎的眼里,一个主宰世界的偶像和一个令人膜拜的明星或大师从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统统不过是某种权力的符码,所不同的仅仅是权力的结构与存在方式。面对他们,一些人接受了说教,一些人接受了诱惑,另一些人接受了奴役。而这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和膜拜--并且,在对权力无休止的竞相膜拜中,膜拜者自己也逐渐成为权力潜在的替身。在此,艺术家不仅以他特有的"法术"使权力者们"现形"--并且进而使权力本身现出了狰狞虚弱的本性。他们--这些通过电脑媒介处理、定格、打印输出的尴尬的权力者们原来同样也是些内心恐慌的可怜虫!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你知道,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全都是些可怜的魔鬼。"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周啸虎这个系列作品时立即联想到了萨氏的这句话。
在艺术家苍鑫的头脑中一直有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理性与感性相互间的纠缠和撕扯。这在他早期客居东村创作的《踩脸》、《病毒系列》等作品中已有所体现,直到若干年前的一次冒犯性行为《扔蛋糕》,和他后一个时期的"炼金术文本"达到一个极端。作于几年前的《舔》后来经过摄影媒介的强调演化为《交流》。在此系列作品中,摄入食物与输出语言思想的舌苔成为演示观念的主体,在品尝种种有关知识、宗教、权力等象征符码--书籍、古币、算盘、金龟、火柴、蜡烛等物品的行为中,艺术家的触须深入到了积淀已久的国人集体无意识之中,"交流"由此而始,然而,一个鲜活的舌苔触及一件件僵死的器具能产生什么样的交流结果这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从那些相同的图象模式中感到却是交流的欲望受阻后的拒斥。如果不是误读,这或许恰恰是作者所欲揭示的当代艺术面临的一种文化处境-一种错位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当代意义上到底有没有出路?由此,苍鑫经过精心设置的"交流"的场景被场景自在的观念逻辑所解构,并走向了交流的反面。但它却道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交流在交流的拒斥情景中所得到的只能是对交流本身的欲罢不能的绝望。这是我们都有过的亲身体会。
这种无可名状的交流的尴尬和失语同时在金锋的影象作品中以另一种形态表述着:一个冷淡的裸体现代少女,一对末日皇族的主仆或一群素不相识金融商客,他们在一些久逝的年代阴森的场景中超时空地相遇。金锋运用了一种近乎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式的法则,将异质的形象叠合在时间敞开的虚拟空间中。那些久已驻留在发黄的照片中的幽魂们神情麻木地注视着这个突然的闯入者--现代裸女,闯入者也是麻木的。她面无表情却又窃窃私语:"我心碎"、"现在这个世界比较乱"、"不能在一起玩",等等,这些通过艺术家的手题写在少女冷淡的酮体肌肤上的话语似乎也隐隐发出一种拒斥的信号,同时又仿佛在施展着一种阴冷的催眠。这种拒斥和催眠的信息暗示了交流受阻后的恐惧与对交流本身的绝望。于是"远一点,再近一点。""远一点,再近一点……"金锋在如此反复的踌躇游移中仍进行着无望却又不得不为之的"交流"。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金锋与苍鑫艺术殊途而同归,在现实与艺术的之间,他们共同体味着交流的尴尬和苦涩。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观念艺术的意义原本是将混沌的意识导入观念的设置与敞开之中,进而达到澄明的境界,而金锋在此系列观念摄影作品中却反其道而用之,错时空的搭配,人与人以及人与场景的对接,显现出一种预设的暧昧和语焉不详。他似乎在问:我们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远一点,再近一点》的作品标题仿佛也在陈述、私语一种作者游移不定的心态,它起到了以刻意的荒诞不经影射同样荒诞不经的文化现实的观念效果。
精神克隆比肉体克隆更耗时日。一个人在历史中与家族面前成像时,他的白日梦能否勾勒出一条十分清析的关于进化的线索是值得怀疑的。当精神家园的口号被一些不名真相的游客一再鼓噪的时候,时代的特征就象一面旗帜,它兼容了来自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种种传奇。我们需要传奇,它是艺术家手中的一根魔棍,它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出奇制胜解释社会欲望的灵丹妙药"这是近年来的"黄岩语录"之一,它被写进了一件仍被称做"黄岩语录"的影象作品中。显而易见,黄岩在运用"语录文体"写作的时候有意识地模访了语录文体的发明者。按照黄岩"越模仿越快乐"(见《作家》黄岩文)的观点,黄岩一定体味到了或仍在体味着许多在揶揄中模仿的快乐,虽然模仿者的文本远不及原创者的文本更为言简意赅。但当这些梦话一样混乱的文字经过电脑数码化的编排进入画面与一张已经通过电脑复制手法加工而成的"克隆"群像合并时,它的意味便立即显现出来。面对这件作品我们需要模仿黄岩的说法:"越混乱越深刻"、"越克隆越可爱""越夸张越刺激"、越重复越有力"、"越庞杂越重要"、越雷同越经典"……。黄岩不仅善于创造一种广为流传的模仿的经典语式,而且善于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印证这种独创语式方法论应用的有效性。在当今后意识形态商业化时代,一个具有知识分子独立人格与良知的艺术家,不仅应当警惕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信念地磨损,同时也要防止权力与商业、技术共谋对其精神的异化和"克隆"。 这应当成为《黄岩语录》所给予我们的真正启示。
在北京艺术家王晋和张大力的艺术中,"摄"与"影"的关系基本上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方式,获得影象的途径基本都是直接拍摄行为或装置,不经电脑处理,一次完成。但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都市的中心,对日益变迁中的街景、城墙以及忽然之间拔地而起的豪华酒店有着特殊的敏感,加之长期观念艺术的实践经验,他们得以创作出一些和城市变化息息相关并具有相当观念性的影象作品。1999年4月的一天,在一处过街桥下,王晋花钱雇用了数名在城市里打工的民工,这些质朴的农民不懂这种杂耍似的游戏为了什么?甚至不相信这种游戏可以挣来他们日常生活的所需。当他们照导演一样的艺术家的意愿站在各自分配好的位置,然后将他们摄入镜头之后,他们一定是在想:今天的钱怎么这么好挣?他们心里一定希望这个顽童再雇佣他们一次吧。至此,王晋的这件作品作为观念摄影还仅仅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他也例外地运用了数码技术。在同一场景照片中,行为的人置换为电脑输出的不忍卒读的无序汉字,它们大大小小的以竖势排列起来象先前的人们,一个顶一个从地面一直接到沉重的水泥桥低面,就那样支撑着站立着。我们不仅要问:王晋要做什么?一群听命于权力和酬金的民众,他们建造过一座又一座水泥城堡,而一堆通过电脑软件输出的文字不也建造了一座座文化的水泥城堡吗?本性上他们一样的盲目而有力量。王晋的《百分之百》所表达的也许就是如此一种观念:现代人所创造的他们赖以生存的文明的壁垒正是被一种盲目的现代力量构筑起来的,人们为此已经付出了异化的代价,人们正在并且还将为此付出代价。
与王晋的多变的艺术策略不同,张大力数年如一日的在大街小巷反复涂绘着一个"张氏头像"。在北京,这个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线描经过长期不断的复制、传播已经在我们的意识中变得不容忽视了,它甚至已经变成了带有某种侵犯性的观念符号。张大力以魔法师的咒语方式数年一语,"破壁"而出,这使得他拥有了一种特权--只要他将他所画在任何一处的头像符号拍下来,似乎就可以作为观念摄影而存在。当然,他涂绘和拍摄之前已经考虑到了影象效果因素:一处废墟与一座新起的摩天大楼重合;一堵残墙以一个张氏头像的造型穿透之后,一座刚刚修缮过的金瓦古殿立于眼前……。这些精心选择的场景经摄影定格后辐射出特有的信息,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中的城市,同时引发我们对这种变化中所存在的问题的思考。一个空洞的头像画了进十年,真可谓十年一剑!这种超人的偏执使得张大力在北京当代艺术界中独树一帜,他以一种超常的个人方式("视觉强奸"?)获得了艺术的公共性。但另一种危险也同时存在于张的偏执之中--一种过分重复的劳作毕竟有悖于艺术家的天性,张大力的"视觉强奸"还能持续多久?再重复下去能否延伸出新的观念意义?因此,张大力已经做出了新的选择。
同样偏执的是南京艺术家管策,对于语言的精妙和感悟在当代或许没有人比他要求的更加苛刻的了。多年来他从照片上做画,对待一张照片相象对待一个情人,他不惜用各种方法反复地揣摩、涂抹、蹂躏,最终致使一张照片变得面目全非--这是管策将摄影照片作为材料来进行语言实验的阶段所运用的一贯方法。但当观念被优先提升到语言材质方法论之上以后,管策对待照片的态度转换为一种戏弄和调情的方式。一些暧昧的话语或是思辩性的语言章节开始进入那些被处理过的照片,与照片中的人物构成一种似是而非貌似亲近的关系,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属性,管策由此说出了内心欲说还休的彷徨和执拗。这些作品显现出当代观念影像艺术中与绘画仍有牵连的一支旁流的美学趣味。多年来,管策正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与一切时尚和潮流保持着警惕和距离的。我们不妨将他作品中依然坚守着的那种类古典的形式语言的完整性看作是对于以观念的名义顺手牵羊的投机者的某种劝戒:艺术是要付出心智和劳动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管策影象艺术中存在着更有针对性的观念性,较之他以往的作品我们发现他的近期作品《手记》系列的观念痕迹已大大超过了他对材料语言的关注,保留下来的"绘画感"也许是由他对摄影照片的某种不信任感、不满足感所致,而这种不信任感与不满足感的存在恰恰是因为观念导入的结果,因为管策的影象作品同样告诉我们的是:视网膜经验的历史已经终结了。
白领阶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理想阶级"成为当今一些向往成功的青年人的奋斗目标。以理论思辨见长并较早从事观念摄影的艺术家邱志杰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一标志着"新时代、新生活""理想人生"的形象符号,并以反讽的语言方式加以表现。邱志杰的影象作品的背景往往空无一物,摄入画面的人物总是衣冠楚楚、笑口常开,戏拟的"文革"动作招式以及显而易见的白领生活礼仪的夸张表演使作品显现出一种对白领阶层"意识形态"的揶揄反讽意味。在题为《好》的一个系列作品中,人物的面部被虚化为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一种非真正电脑技术所为的手绘马赛克面具,它们被表演者带在脸上,从视觉上对观者的视网膜经验和庸常判断力形成恶毒的嘲弄。他所要强调揭示的似乎不仅仅是当代人非个性化的技术克隆属性,而是企图通过表层的社会学批判显现他真正的艺术观念:以手工技术戏访电脑技术的无所不能,并由此还原技术对人类异化处境的真相,进而达到确立其艺术方法论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邱志杰的艺术诡计。
与邱志杰同属"浙系"的蒋志近年来在小说和艺术上都有所成。作家、艺术家双重身份使他与文学艺术两个圈子都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无从考察玩偶"木木"——一个童话般天真朴拙的布质公主造像何以成为他的摄影主体,但从他以"木木"主体形象的摄影作品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内心敏感艺术家在商业时代嘈杂的城市生活中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追忆。在以"木木"命名的系列作品中,蒋志让他的小主人公"木木"渺小的身躯或孤独的立于苍茫的河边;或隐现于粗砺的树洞之中;抑或置身危险的锅炉前,作者运用了中国传统诗画美学中的借景手段,将仿佛来自童话中的无名公主安置在与童话世界不同的外部现实场景中,与之构成一种类似文学的叙事性关系,巧妙地创造出一种与当代生活相关的视觉童话。如果说他带有文本实验色彩的小说《雪儿》表现出的是作者的某种无奈又迷恋的"玩世"心态的话,那么,他的"木木"系列摄影作品则折射出作者面对他无所适从的现实深存于内心的惶恐不安和对"超世"的向往。
马建最好的影象作品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他引以为得意的他以"新郎"姿态偕"新娘"莫娜丽萨出现在各种场合的《有约北京》。此作之所以讨好是因为它完全沿用了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最流行的创作手法:中西形象并置,古今符号对接,而且挪用名作又能满足具有基本美术常识之人的欣赏欲求。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其一,观念艺术家应当尽量回避业已流行的创作手法,其二,莫娜丽萨在这件作品中的煽情力量已大大得超过了做为影象观念作品所应提供出的智性。相比而言,他的《被奸者》系列则更为优秀。在这一系列黑白图像中,艺术家本人的形象经电脑数码演化被巧妙地嫁接到正被一部分人有意淡化或篡改的"文革"场景中。这是一种重返历史的姿态。在《被奸者》者中,马建的头颅被那些"革命"的施暴者们按倒在地,施暴者的面容被推至画面之外,以此强化了施暴者的抽象性。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在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我们可以忽略画面中提示出时代特征的仅有的一个汉语称谓(被奸者)的话,无论是哪个时代,一个人同时既可以是被奸者又可能是施暴者,因为丧失理性尺度之后,无论任何人都是这两者的潜在替身。在真实与虚拟之间,艺术家"亲身"感受着当年的疯狂恐怖。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马建这种重返历史的观念创作的当代意义便是不证自明的。况且"文革"至今并不久远,而且至今仍是某种有待深究的学术禁区。显然,马建的《被奸者》比前一时期同样利用"文革"资源创作的"政治波普"的某些作品更富于内在的观念性,或者说其观念设置与显现更有深意。它唤起了我们的记忆中隐伏的伤痛,使我们再次面对并反省被偶像强权愚弄强奸的耻辱,进而深思存在的荒谬。
另一种激发我们记忆的方式在艺术家庄辉近年来的摄影创作中不断重复着。多年来他象一个谋略在胸的掮客或导演,伙同技术精良的照相师扛着一大堆摄影器材东奔西跑,在农村、工矿、企业乃至学校、军队拍下一群又一群人的合影。在这些貌似老照片的以手卷形式存在的摄影作品前,也许人们首先会产生一个疑虑:这是艺术吗?这就是当代艺术吗?(是否当初庄辉拿到第一张集体合影照时也曾有这样的疑虑?)一般来讲,在信仰失落的年代,能把如此众多的人召集一起的东西只有两个:权力与金钱。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庄辉是怎样披挂上阵,动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联络,说服那些往往自以为是的单位部门的官员们组织起全部人马接受他的摄影检阅的。可能整个过程类似克利斯多为包扎帝国大厦而游说的方式,但庄辉所得到的结果却仅仅就是一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一般摄影师常拍的集体合影。但他却自信地称之为作品,并成功地送到了威尼斯双年展。毫无疑问,如果不进入观念之思,人们便不可能理解庄辉的摄影。从这个意义来讲,庄辉的摄影是真正的观念摄影。在这些大同小异的集体合影照片中,由于强制性的拍摄距离,一张脸与另一张脸几乎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原本生动鲜活、充满七情六欲的具体的个人被一个"集合"的指令轻易地抽象、简化为群体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里的"一"与个体独立的"一"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是唯一的"一",而前者则是统一的"一";前者可批量克隆,而后者则不可替代......庄辉这些貌似平庸的集体合影真实地反映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普遍的精神与存在的状态,并达到了一种客观真实与观念真实的有机结合。如此理解,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当岁月流失的愈久,它的意义就愈加凸显,它将唤起未来人对一个消逝了的久远时代的记忆--艺术见证的力量由此而生。
将数码影象技术应用于观念创作的还有北京艺术家赵半狄和经常穿梭于于北京、济南两地的艺术家高氏兄弟,前者将行为化的图像转换为具有公共传播功能的公益广告招贴,后者则以图像装置方式表达着他们超出艺术界域的人文诉求。前者是温情、乐观的;后者则是冷峻、近乎绝望的。前者广为流传的几件公益广告以灯箱装置的形式被安放在了车水马龙的地铁中,使不少人因此发现前卫艺术并不全是洪水猛兽。在赵的系列作品中最使人感动的是一件反映下岗工人处境的作品《下岗》,"我下岗了"、"送你一个礼物他能让你看的远些。"赵半狄在这件影象作品中通过这仅有的两句对白和仅有的两个演员的身影上演了一幕令人不无伤感的独幕剧--主人公1(仍是艺术家自己)面部朝向画面的景深,他凄楚孤独地眺望着桥下公路上急驶而来的汽车;主人公2(仍是那个著名的熊猫咪咪)面朝失业者。作品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寻常故事,并观念性地提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日益缺损但却异常重要一种感情--爱与同情。值得深思的是,在赵半狄的故事中这种爱与同情没有来自我们人类,而来自一个无法真正给人慰籍的人造玩具。
中国新闻系列"是高氏兄弟《有关历史、现实与文化的数码演化系列》中的子系列,或称"媒体批判系列"。在这三联作品中,艺术家通过数码强化的图象直接性地宣示出:当今世界多元化的视听信息在意识形态机器的过滤中被无奇不有的商品广告和插科打诨的无聊笑话所充代,经过权力筛选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以"糖衣炮弹"式的媚态软化正在日益加剧的钱权交易、贫富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给大众原本平庸的生活提供廉价低劣的精神食粮。进而,即时性的消费鼓噪所制造出的低级快感分泌物又催化出无限膨胀的欲望,从而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始终处在一个低级蒙昧的水准。缘此,对驯化工具的象征物--电视的反抗与嘲弄便成为此系列作品存在的理由。它要诘问的是:当今具有全权意识形态属性的大众传媒给予我们的承诺有多少是可以信赖的?"我们还能相信什么?"(《电视马桶》)"我们能得到什么?"(《电视谎言》)"我们还等待什么?(《电视寓言》)"在此,电脑语言的功能被用来简化了原摄影画面中的一切不必要的细节,从而强调突出了一种具有观念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应当说明的是,观念摄影在中国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艺术潮动,与同时兴起的录象艺术、网络艺术一起正以变化、发展、多维的态势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影响着人们对以往摄影与艺术的概念的看法。是否可以说,以观念的名义,摄影在摄影界以外--当代艺术界正在进行一次观念性的革命?我们姑且称之为观念摄影新浪潮。本文之所以用较大的笔墨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品评,是因为我们认为构成观念摄影艺术新浪潮的基本因子和最重要的基石只能是具体的观念摄影作品,如果没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考察就不能真正看清蕴涵其中的可能的潜力,更无法从宏观上充分把握摄影在中国当代艺术媒材变革时期的真正意义,当然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应有的评价。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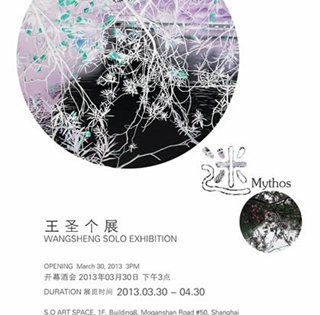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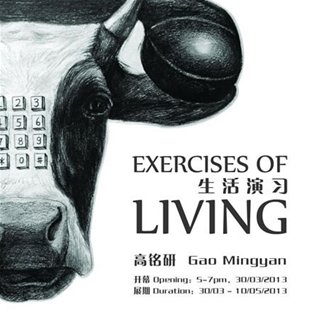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玩光影:
玩光影: 清水出芙
清水出芙 户外运动
户外运动 轻松几招
轻松几招 胶片摄影
胶片摄影 李少白经
李少白经 一定要靠
一定要靠 掌握好“
掌握好“ 栖息处打
栖息处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