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戏曲真的艰涩乏味吗?显然不是。单说《闹天宫》,满台的真功夫,就算你不懂,也能看个热闹吧。但事实怎么样呢?我们剧团的小剧场最多可容纳两百余名观众,平时周日演出,来个二三十人已是可喜的了,台上比台下人多是经常的事。话又说回来,记得有一次,为一群驻沪外国领事的夫人们表演,我们现场演示了旦角上妆的全过程。在我们眼中,一个半小时的化妆穿衣,早已习以为常,可是那些领事夫人们却惊叹不已,每贴一个片子都询问半天,直呼“Wonderful”! 
有时我会想,面对现代社会品质和品位都在提升的舞台,古老的昆曲应该有怎样的表达?呈现怎样的面貌?如今的上海昆剧团,已经有了累积10年“昆曲走近青年”的方法和经验,同时,它还兼顾传统老戏的抢救和古典新编剧的创排,以及像全本《牡丹亭》、《长生殿》这样的大制作。社会在变,如果我们只是固守在自己的空间里,是不行的。
所以,为了吸引年轻人关注昆曲,我们开展了“昆曲走近青年”活动。在同济大学演出大获成功之后,我们用这样一场普及性互动讲演晚会的模式,走遍了几乎申城所有的高校,以10年300余场的记录,创下了上海昆剧团单项演出之最,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记: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环境下,昆曲同样面对着诸多影响,您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这对昆曲会有什么影响?
张:为了工作需要,我得翻看很多昆曲表演艺术的资料,包括书和影像,得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背台词、练身段。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将决定他的精神状态,所以我的生活应该更加丰富多彩,而不是只有昆曲。我有很多业余爱好,虽然挺花时间和精力,但都让我十分享受。我对新鲜事物高度敏感,而高速发展中的上海、中国乃至全世界,又是如此多元。虽然昆曲历经600年的积淀,本身已非常丰富,但是我觉得不能那么单一。我要接触各类资讯,从中吸纳更多的新知识,而这些都将会对我的昆曲表演有所帮助。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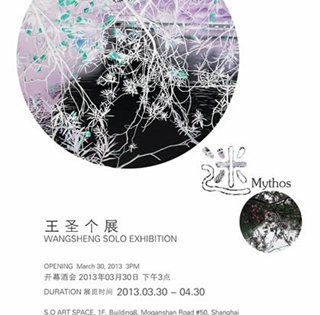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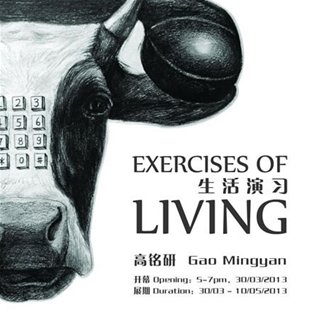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全明星版
全明星版 2011年全
2011年全 赵本山春
赵本山春 大剧院首
大剧院首 大剧院虎
大剧院虎 金秋10月
金秋10月 雷子乐笑
雷子乐笑 用青春拥
用青春拥 胡锦涛等
胡锦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