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汪曾祺说铁凝的小说是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如今的中国作协女主席铁凝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铁凝评传》对铁凝的生活和创作历程进行了梳理,试图打开一个女性作家心理和创作的隐秘通道。

资料图片

曾指责母亲“对毛主席一点都没有感情!”
铁凝1957年出生于北京。铁凝的童年就像其他的女孩一样普通,她甚至感到自己在同年龄的伙伴中是比较不聪明的。
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吧,她寄居在北京的外婆家。有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孩经常来她外婆住的四合院玩耍,男孩站在门口,以一种轻蔑的神态不屑一顾地评论着胡同里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太贫,那个女孩太贫。铁凝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哥哥,你觉得我贫吗。男孩回过头来,瞧了瞧这位黄毛丫头,说,你呀,还不算太贫,就是有些分贝。铁凝满眼疑惑地问,什么是分贝。男孩说你回去自个儿想吧。这个问题折腾了铁凝一晚上,弄得她满脑子的浆糊。第二天,她只好再次来到男孩面前羞惭地说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分贝。男孩坏坏地笑了,启发铁凝说,会写贫字吗,上面是个什么字,下面是个什么字……
家庭对铁凝的影响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这是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氛围的家庭。父亲铁扬是一名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一名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
铁凝的父亲有一个习惯,当家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作出决择时,就把全家人召集起来举行家庭会议。事实上全家人就是四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铁凝两姐妹。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没有什么禁忌和约束,铁凝的思想和性格得到了充分自由的成长。
她还记得“文革”中有一天,她大概十来岁吧,她的父母在悄悄地议论政治,话语里也涉及到毛泽东,铁凝在一旁听到了,这使她大为惊异,他们怎么能够对毛主席表示不满情绪呢?她暗暗生气,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根本不理她的母亲。母亲问她,你怎么不同我说话呀。母亲的问话终于使她有机会把憋在心里的不满发泄出来了,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你对毛主席一点都没有感情!
处女作想象镰刀 “飞”了起来
母亲想培养她搞声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铁凝本人似乎迷上了舞蹈(大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爱好)。她曾每天到一位舞蹈老师那儿练习舞蹈基本功,后来还曾考上了艺术学校舞蹈科,但铁凝最终选择了文学。
铁凝说她上学时最喜欢作文课,而数学、物理、化学这类课程却理所当然地不行。铁凝回忆说:“八岁的我已开始写日记:‘妈妈让我去买菜,我买了一个胖冬瓜……’父亲很看重我用的这个‘胖’字,不知这能否算我形象思维的一个兆头。”
她正式发表的处女作是她中学时代写的一篇作文。学校在一次“学农”归来后布置了一堂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学农劳动”。铁凝将这次作文当成了一次愉快的写作,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大作文。她还擅自给自己的作文起了一个题目:“会飞的镰刀”。铁凝写一个乡下男孩和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的友情。城市里来的女学生们第二天要去割麦子,乡下男孩为了帮助这些不熟悉农活的城市女学生,当夜晚大家都入睡了的时候,他悄悄地拿走大家的镰刀,为大家磨镰刀,女学生们醒来时突然发现镰刀怎么“飞”走了。在那个思想极端禁锢的年代里,铁凝竟然能想象着镰刀 “飞”了起来,这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而当时的铁凝才十七岁。第二年,这篇作文被收入儿童文学集《盖红印章的考卷》中。
父亲与徐光耀是好朋友。那时候大作家都在挨批判,徐光耀同样难以幸免。所幸的是,当时上面要写一个歌颂先进的报告文学,需要写作的高手,就想到了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耀,把他从农村召回来了。父亲挑了铁凝的这篇《会飞的镰刀》,还有另一篇作文,带着铁凝去见徐光耀。
多少年后,铁凝还会经常提起与徐光耀的这次见面。“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这句评语,不啻是一股巨大的风,鼓荡起她的文学梦想。铁凝说过她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当作家的妄想”,听了徐光耀大作家的话,她就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为当作家,放弃当文艺兵和上北大
与徐光耀见面的第二年,铁凝高中毕业,她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当时还是“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后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此时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名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但是,铁凝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她当作家的梦。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尚在农村的铁凝也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望去上大学,而且她觉得要读就得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就揣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跑到北大,她将小说交给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申述说她的数学不好,但能写小说,能否给以特别对待。后来北大中文系还给她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欢迎你来中文系学习,希望今年就报考。但河北的老作家们劝阻铁凝留下,他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那你是想当作家呢,还是想当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呢?铁凝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当一个作家。铁凝最后放弃了上大学的努力。
毫无疑问,铁凝给父母出了一道难题。母亲坚决不同意,她一次又一次伤心地哭泣,又疼又恨地望着女儿,气哼哼地说,你就去当你的“女高尔基”吧。那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唯一能够公开推崇的作家大概就是高尔基了,母亲对女儿的痴迷文学无可奈何,只好把气撒在“高尔基”身上。你去当“高尔基”吧,而且还是女的“高尔基”。
下乡的“风光”背后有“鬼祟感”
1975年夏天,应届毕业的中学生照例有一大批作为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农村。铁凝也是其中的一位,但由于她是放弃了当兵的机会,主动提出下农村的,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她的事迹,她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主动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生活的革命青年,并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用”。
铁凝的下乡非常风光,得到了一系列的社会荣誉,但这一切并没有使铁凝感到兴奋,反而忐忑不安。她后来用一个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鬼祟感。她总觉得自己到乡下来是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即使到了乡下,她也把当作家的愿望悄悄藏在心底。
从1975年下乡,到1979年调到保定地区文联,她在农村生活了将近四年。可以说从这里铁凝自觉地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个人的文学创作,所有的文学刊物也停办了。直到1972年左右,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文学上也有所松动,但那时候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所谓的“三结合”创作小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但是,才十八九岁的铁凝却在河北的乡村认真地迈出了文学的步履。
下乡四年她差不多写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札记。大大小小的日记本一直被她收藏在一个大木箱里,这个木箱是父亲在她下乡前亲手为她做的(父亲说画家就是劳动者,他经常自己动手做一些木匠活,在那个提倡一致性的年代,家具的样式往往也是各家各户一模一样的,铁凝家里的一些别致的家具就全是出自父亲之手)。后来铁凝离开乡村,就把这口大木箱随身带回了城里,她将木箱摆放在她的书房,与那些造型现代的家具很不谐调地相处在一起,木箱里仍然装着那些日记本。
孙犁说,《哦,香雪》从头到尾都是诗
1982年夏,《青年文学》杂志在青岛举办文学笔会。铁凝在笔会上写出了《哦,香雪》这篇短篇小说:火车开进了深山沟,现代文明的鸣叫唤醒了藏在山村姑娘心中的精神向往。小说中十七岁的香雪,走了三十里的山路,用四十个鸡蛋换来一个她向往已久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这个主题虽然不新鲜,但对于一个长年纠缠于政治化的中国文坛来说是久违的新意。
小说稿交出来后,没有引起主办者的欣喜。因为当时的文学主流仍然笼罩着浓浓的政治气氛。
小说发表后,铁凝将载有这篇小说的《青年文学》寄给了孙犁。孙犁一直身体有些不适,所以拖了一段时间才阅读,但他读完《哦,香雪》,马上就给铁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1982年12月14日。孙犁在信上说:
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1983年年初,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评奖工作已经开始了。《哦,香雪》在《青年文学》发表后,《小说选刊》迟至1983 年1 月才予转载, 又未放在头条位置。年初,短篇小说奖的评委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哦,香雪》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到第一批备选篇目中。就在这个过程中,孙犁给铁凝的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小说选刊》在第2期上也转载了这封评价《哦,香雪》的信。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据当时参与评奖工作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1983年1月24日,由于《小说选刊》选载《香雪》已为读者和评委得知,提供第二批16篇备选作品时,《香雪》被列其间,但1月29日进行的第一次评委会,没有提到《香雪》。2月26日举行的第二次评委会,《香雪》虽被提到,但大都是放在发言的最后。起先,沙汀在发言最后特意表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哦,香雪》。’接着,冯牧、唐、王蒙等一些评委,相继都在发言最后表明:‘个人偏爱《哦,香雪》。’唐还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再次发言,特别说明:‘我个人偏爱《哦,香雪》,原先不敢讲,既然有人讲了,我就提出来把它的名次往前排吧。’王蒙则明确提出,将这一篇提到前五名——按照惯例,前五名实际上也就是一等奖。”
《哦,香雪》是铁凝的成名作,是“铁凝艺术世界中第一个被公认的、成功的美的形象”。它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饱受挖苦的书名“大浴女”,取自塞尚名作
1982年,25岁的铁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铁凝从保定地区文联调到河北省文联,成为河北省文联的专业作家,同年,铁凝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84年底,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界是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地方,此时的铁凝才27岁,就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理事。
2000年平平常常地来到,但是对于铁凝来说,这一年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她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大浴女》正式出版。
据保守的估计,《大浴女》于2000年3月正式上市,第一版就印行了20万册,但这些宣传造势带给铁凝的恐怕多是负面的影响了。因为这样的宣传造势完全是畅销书的营销方式,这使得人们都把《大浴女》作为畅销书来期待,甚至人们在这种期待中不乏微辞,似乎对铁凝为什么要屈从于市场去做一名畅销书作家而表示不解。
《大浴女》的这个书名也成了媒体做文章的“热点”。“瞧瞧人家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正在洗澡的成熟女性。在评论家笔下,可能具有无限的艺术张力;而在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眼里,则具有十分广阔的联想空间,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个能畅销的名字。”这样的挖苦讥讽的文字就出现在当时的报端。
三四年之后,铁凝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仍然很诚恳地说到这个书名,她说:“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女出浴,所以,好多人认为是一部通俗作品。我当时想不出好名字,又迫切地想写这部长篇,小说完成之后还是没有名字。偶然看到了塞尚《大浴女》这组绘画作品,我觉得它很好地契合了我小说的精神内核。塞尚的《大浴女》组画,画面上都是洗澡的女人,女性的裸体是褐色泥土一样的颜色,跟大树纠缠在一起。画面非常有气势,象征着精神的涤荡,很有震撼力。我接触绘画比较早,对西方现代派的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都有一些了解,所以,那些画面不能让我觉得新鲜和诧异,我想到只是它和小说的契合。后来一些作家和读者都表示不大能接受这个名字,这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但现在让我换个名字我也真换不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书名暗示出这部小说的主题,它是作者一次灵魂在场的精神洗浴。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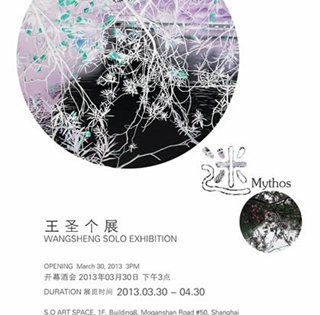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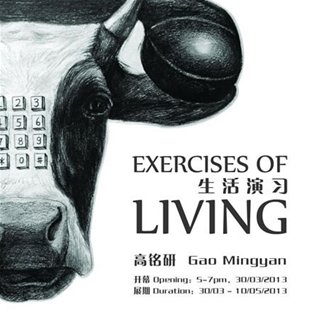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龙应台:
龙应台: 铁凝:十
铁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