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是戏曲大家族中的“小辈”,在20世纪50年代登堂入室以来,不断吸纳新鲜养料,不断发扬自身特有品格,终于成长壮大,成为支撑优秀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梅戏是一个具有通俗品格的戏曲剧种,它的通俗品格强烈地表现在音乐上。在黄梅戏发展源头,湖北的“黄梅调”、安徽的“采茶”、“花鼓”以及当地的山歌小调就是极其通俗的民间音乐。尽管黄梅戏在发展成高台大戏的过程中,音乐方面接受了板腔体的整合,但却令人惊奇地保持了通俗平实的风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黄梅戏的这一过程基本上是在乡村演出中形成,观众的欣赏趣味支配着创作者。另一方面,从艺人员的技艺有限,这使得他们放弃繁文缛节的炫技而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发挥天才。“融南合北”也好,“洋为中用”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丰富黄梅戏音乐的表现力。
人们在谈到黄梅戏音乐的时候,常常用“好听”、“听懂”、“好学”来归纳它的特点。而一些不懂汉语的外国友人,则将黄梅戏说成是“中国的乡村音乐”。黄梅音乐的浅易性特征,增强了剧种音乐与观众的亲和度,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就是这种亲和度的具体表现。我们注意到,与当今仍然活跃的某些大剧种相比(如京剧、豫剧、越剧、评剧、川剧等),黄梅戏的唱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音区不宽,男女腔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大六度至大九度。二是拖腔较少,即使有拖腔也是旋律平滑,少有做腔做调。三是慢板不慢,快板不快,虽有例外,也是凤毛麟角,整体音乐的张力适度。四是语言易懂,虽占有地利,但与黄梅戏的从业者不断调整舞台语言有意识地与普通话比较,心里想着全国观众的理念有关。五是黄梅戏的旋律覆盖面广,集中体现汉民族共同的音乐感受,换句话说,黄梅戏音乐之所以适应大众欣赏的共同标准,是因为它将自己的特色与共性较好的地统一起来。黄梅戏音乐的这些特点,不仅使它与别的剧种音乐区分开来,重要的是,黄梅戏作为通俗戏剧的代表,在音乐上具备了通俗的品格,需要提起的是,黄梅戏的通俗性一直是关心中国音乐戏剧走向的人士念念不忘的品质。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在给余秋雨先生的信中表示:中国歌剧的发展要从地方戏曲中寻找出路,从黄梅戏中发展中国的音乐剧可能性更大。黄佐临先生如此看重黄梅戏,是黄梅戏的大众性、可塑性、质朴性以及独特的美感使然。
在中国戏曲音乐的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较大的风格转型。如明代的昆山、海盐、余姚、弋之外有“花部”盛行并最终以花胜雅,今天的京剧被视作“国剧”之后地方戏的割据与扩展等。这些变化中,有一个共同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凡是某一剧种的初始之际,其音乐总是来自民间,有着明白流畅的天然禀性,而当初露头角,剧种的发展受到关注——尤其是受到社会的上层关注之时,它的发展方向很容易趋向繁难,往往在“完善”的目标达到之后,成为曲高和寡的一类,被少数人奉养而渐离大众。然后,又一个音乐来自民间的剧种从头做起,继而盛,再而衰······
应该说,时至今日,黄梅戏音乐在主体上仍然保持着通俗戏剧的品格,但在黄梅戏音乐今后的发展方向上,人们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认为,黄梅戏音乐比较单调必须有人去丰富,而发展的方向是向歌剧靠拢。他们主张音乐的交响化,主张唱法的大幅度改变。另一些人则认为,黄梅戏来自乡村,这股“山野吹来的风”最可贵的是乡土气息,主张音乐保持“原汁原味”,理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些主张都含有合理的成分,都是发展黄梅戏音乐可供参考的意见。问题是,这些意见应该置于黄梅戏音乐总体风格之下,在大众情趣、时代气息方面做足文章。而不能只顾突围,不问方向,犯南辕北辙的错误。我们以为,为了黄梅戏音乐未来的健康发展,思考一下艺术语言表层的浅易与内层的深刻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关系,思考黄梅音乐如何达到单纯而不单调、简洁而不简陋、通俗而不庸俗的高品味大众音乐的境界是有现实意义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传统黄梅戏音乐在浅易与深刻的统一上有怎样的作为。在“主腔”中,以[男平词]、[女平词]与[男二行]、[女二行]和[男八板]、[女八板]及[男三行]、[女三行]这“四组八曲”再加上“迈腔”、“行腔”两个“替代腔句”和“散板”的板式变化与“滚腔”的腔句扩充,基本上提供了戏剧所需要的区分性别、变化节奏、叙事抒情等音乐表现功能。这些腔体的旋律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流传、易变化发展,在表层上是浅显的、通俗的。但这些腔体各自有不同的表情、不同的趣味,又因速度的变化,腔体的转接、旋法的改变等创腔手段的综合运用,在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尤其是戏剧化的心理流程上有深入人心的表现力度。我们再从演唱看优秀的黄梅戏艺术家是怎样做到浅易与深刻的统一的。如严凤英的演唱,其效果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像唱一样说,像说一样唱”亲切自然,落落大方。然而,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严凤英却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她对黄梅戏女腔的润色,细腻而不做作,丰富而不繁难有定式而不僵化,藏巧于拙,浅易之中尽显深情。据与严凤英合作的很多作家、作曲家、演员介绍,她在琢磨唱腔的过程中就像着了魔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不仅在排练场用心揣摩,就是旅途中,在家里的起居室,厨房中,也常常“曲不离口”,达到痴迷的程度。严凤英唱法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她以明白如话的音乐语言,传达出人物心中深切的情感体验。严凤英的浅易在于与大众对话的表象特征,严凤英的深刻在于对大众情感的深层唤起。
我们知道,音乐在情感表现上有巨大的力量和不可替代的直接性。不仅现代的音乐学家认为“音乐内容主要是情感内容”(于润洋语),“音乐,在伟大的作曲家的笔下,用纯属他个人的表现方法最完美地表达了人类普遍感情”(柯克语)。古代贤哲们也早已阐述过音乐的表现功能,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乐调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反映出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互相对立的品质和其他性情。黑格尔也认为情感才是音乐所要据为已有的领域,他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的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程度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乐记》已提出:“凡音之起,凡人心生也”。并论及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这六种不同心情是如何通过音乐来表现的。音乐和戏剧的结合,也是音乐可以描功人物的情状,渲染不同的情感扭转,激发和引导观众的感情倾向的功能使二者走到一起。黄梅戏音乐的作用,首要的也是表情。即使在叙事性的唱腔中,也包含着剧中人的情态,包含着叙事过程中丝丝入扣的心情解读,因此,我们把表情的深刻与否看成黄梅戏音乐的灵魂,并且想念深刻的表现并不等于一定要繁难的外化形式,浅显易懂的唱腔可以达到表现人物深层的情感起伏的目的。在这里,艺术家们的思路应该是:在体验人物的情感上深入深入再深入,在表达情感的方式上浅出浅出再浅出。这情形就像毕加索色勒的那条公牛,线条从繁到简,最后达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我们所说黄梅戏音乐浅易与深刻的统一,决不意味着在表现形式上的呆板音调与内容上的故作深沉。我们所说的深刻是指情感表达的深度,是“情感”而非“理深”。黄梅戏音乐浅易的品格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今天看来是通俗易懂的音乐表现形式,昨天可能被人们视作异端,而明天则有可能被看成简陋。艺术之路常变常新,黄梅戏音乐也不例外。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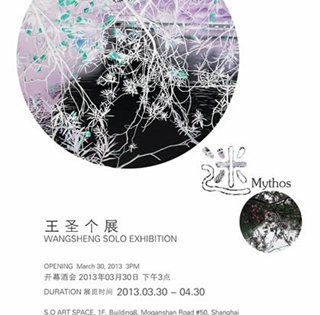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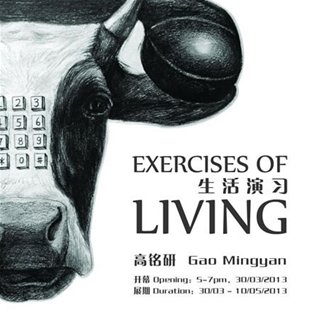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