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以民间狂欢仪式为内核的乡村原生态戏曲不是审美意义上的成熟戏曲演出,从审美功能和角度无法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评判。它是粗俗的、原生态的生活样式本身,与精雅的、成熟完善的戏曲表演艺术相对立,它也是乡野村民传统的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的载体,与文人视野和官方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审美标准相对立,是远离都市的偏僻乡野在其自足空间内有限度的狂欢。
然而,即便是有限度的狂欢,由于戏曲本身的传播功能,又由于乡村远离中心偏于一隅的地理环境,更由于职业艺人的分化,乡村原生态的黄梅戏声势日渐壮大,影响日渐深远,遂引起官方的注意。”一种剧种,在村坊小戏阶段,统治阶级是不会注意的;一定要等到它发展壮大,进入都市,才引起他们的注意。”在官方意识形态视野中,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和戏谑的动作表演以及仪式与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有悖风化,即有碍于他们制定的秩序与规范,必须加以禁止,而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这些原本是乡野村民狂欢仪式的原生态形式则被视为粗俗与野蛮,即与他们确立的审美标准不符,甚至背道而驰,必须加以删改。”禁戏”的尺度与”删诗”的尺度在对待乡村原生态戏曲的方式上总是不谋而合,其中最为本质的原因乃是乡村原生态戏曲传达的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性因素是他们眼中的”异质”。
“从传统上说,狂欢节庆祝的是混乱,并允许在一定时间内随心所欲。”混乱是官方意识形态视野中的”异质”,而粗俗则是文人士大夫精雅艺术观照下的”异质”。
我们从老艺人口述本《闹花灯》和《打猪草》到改编后版本的演变中看到乡村原生态形式的黄梅戏是如何改变其本原面目而成为越来越精雅化的审美戏曲样式的。由于被作用的是”官禁”和”删诗”尺度,那些最具指示性的有悖风化的成分与粗俗的对白、唱词与表演遭阉割,在从纯粹的民间狂欢仪式中抽离出来独立成戏曲样式的过程中,最初的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性因素由于艺人的加工改造相对弱化,现在,经过大幅度删改,原生态黄梅戏民间狂欢仪式性因素更加薄弱而且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但相对于黄梅戏日益成熟日益精雅的后期剧目,即便是经改编的《闹花灯》和《打猪草》在乡村演出形式中仍然显示出民间狂欢仪式的特质,原生态黄梅戏”化石”的”硬体部分”仍是被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从经”风化”的原生态黄梅戏”化石”中窥见其大略情状,这就是经改编后黄梅戏《闹花灯》和《打猪草》的剧本形态和演出形式等多种因素显示出的狂欢性——狂欢式娱乐仪式表演与民间狂欢性生存体验。
三
大约十几年前,也就是在电视尚未在乡村普及时,每年的春节到元宵期间,是安庆各地乡村黄梅戏”演出”集中的时节。说是”演出”,实际上是集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性于一体的”全民”狂欢式生存。戏曲表演总是伴随着传统民俗中的狮子龙灯于一体的形式进行,是春节村民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与狮子龙灯形式相结合外,它还与锣鼓鞭炮这种热闹的声音语言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与兽(拟兽)、声与光混合的声音的交响、色彩的交织与形体的交融,是一种典型的乡村民间狂欢仪式。”最晚从19世纪起,狮子龙灯就被当成了中西交流的文化橱窗。与西班牙节日的人牛相斗和巴西节日的纵情狂欢不同,中国人耍狮子、舞龙灯是一种人模拟兽的表演,带有严肃的仪式性质。
据研究,它的意义有绕境祭祖、迎神赛社、求子添丁、春祈秋报、联络村户、公平竞争、象征机会与幸运的圣物等多种,其威力来自狮子和龙两个神兽的降临,以及由锣鼓鞭炮所象征的它们的冲天大吼与现世权威。”与狮子龙灯的仪式性质相似,我们在老艺人口述本《闹花灯》中,看到了乡民迎神赛社、求子添丁、祈报平安吉祥(如十盏灯的数字象征意义)的内容。如果说狮子龙灯带有严肃的仪式性质,戏曲表演则相对具有娱乐狂欢性;如果说狮子龙灯更具娱神色彩,戏曲表演就更具娱人功能。由非职业性乡民自己组织演出的戏曲表演并不含有太多审美成分,其民间狂欢仪式功能远甚于戏曲的审美功能。
与城市广场和剧院演出场地不同,乡村黄梅戏节庆戏曲表演是挨家挨户进行,演出场所多为厅堂和场院。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安庆地区农村所有的狮子龙灯都必须在厅堂例行传统的参拜仪式,因为厅堂是各家祖先牌位所在地,是家庭乃至家族的中心,戏曲表演则不一定在厅堂。而常在场院或屋外露天的谷场,更没有任何的参拜仪式。这也表明,狮子龙灯更具祭神功能,而戏曲表演更具娱人功能。在这个自足的娱乐狂欢时空中,由于”演员”与”观众”是在同一空间同一平面进行,使得传统戏曲观演关系中观众与演员处于一高一低两个不同平面不同层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被打破,演员与观众之间的隔阂消除,”演员”是来自”观众”中的一员,演员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的不是”角色”的身份,而是这一集体中熟悉的一员的身份。这熟悉的一员由于扮演了一个非现实的角色而具有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倘若这”熟悉的陌生人”——”角色”是大家全然不熟悉、严肃无趣甚至忧郁悲哀的角色,他们在其中感受到的娱乐功能也一定会被陌生的新奇感和悲哀的心理所代替。确实,这”熟悉的陌生人”本身也是他们极为熟悉的——我们知道,在每年的春节乡村戏曲演出中,表演的剧目多为《闹花灯》和《打猪草》,乡民们不仅已经看过无数遍,甚至每年、每夜都会看很多遍。从这一角度看,乡村节日戏曲演出也具有重复性的仪式表演特征。因此,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本身——被扮演者,即”角色”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她)就来自”我们”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式、”我们”的生存状态。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版本中对同一”角色”的称谓也不相同,以《打猪草》为例,余本中生、旦分别称”陶四女”和”金三伢’,陈本中称为”陶金花”和”金三矮子”,而改本则称做”陶金花”和”金小毛”。
这些称呼都带有普遍性、非确定性,是”我们”中的任意一个。因此,不仅”观众”和”演员”,甚至”观众”和”角色”都是熟悉的、亲昵的。一句话,”我们”是一体的。这种无阻碍无隔阂的”一体”性特征是通过仪式表演与娱乐狂欢融合到一起的:《闹花灯》里的”王小六”一边指着观众中的任一人一边假装生气并带有戏谑性说:”你这个人不看灯光看着我老婆干什么?要是我也不看灯光看你老婆,你生气不生气?、”——那些以为指的是自己的”观众”(注意,戏里的观众与现实的观众已合二为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王小六”笑了,”观众”们也全都大笑起来。在这里,演员与观众之间不再是被动的观看与主动的表演关系,而是互相嘲弄、人人表演的对等交流,若说”演员”与”观众”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便是主与从的不同,而非主与客的对立。
我们说过,即便是经删改加工过的改本《闹花灯》和《打猪草》,它们被剔除了最具民间狂欢内核的插科打诨式因素、粗俗的骂人话、戏谑的动作与仪式性、民间意识形态性唱词,但比较黄梅戏后期日趋精雅化文士化的成熟戏曲剧目,其对白、唱词、唱腔乃至表演因素依然具有明显的民间狂欢仪式色彩。
《闹花灯》和《打猪草》的基调是民间娱乐狂欢性的”笑”,它最直接的来源是角色带有喜剧色彩的滑稽幽默的言语动作表演。《闹花灯》夫妻二人正欢天喜地赶去看灯,妻子突然撒娇生气说不看灯了,当丈夫得知原来是有人不看灯而只看着自己的老婆,便指着观众半嗔半怒地”责骂”起来,这样的情景令人发笑;夫妻二人喜形于色地欣赏着各种各样的灯,当看到”乌龟灯,头一缩,颈一伸,不笑人来也笑人”时,便”笑得我夫妻肚哇肚子疼”,一边唱一边捧腹大笑;夫妻二人正兴高采烈地看灯,丈夫突然指着妻子的裤子惊叫”不好了,不好了,老婆的裤脚烧着了。”‘老婆吓得变了脸色,定神一看,原来是丈夫在吓唬自己,便半嗔半怒地骂丈夫是”砍头的”。这些戏谑性令人发笑的言语动作表演简直就是巴赫金狂欢学中具”贬低化、世俗化、肉体化”特点的怪诞现实主义的形象化与具体化。
《闹花灯》《打猪草》以人物滑稽幽默的言语动作表演再现了民间狂欢仪式和狂欢式生存体验,其狂欢式场景也是民间狂欢仪式的本质再现。《闹花灯》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灯,更有拥挤的人群:”长子来看灯,挤着头一伸。矮子来看灯,挤着往下蹲。胖子来看灯,挤着汗淋淋。瘦子来看灯,挤着一把筋。”在胡本《闹花灯》中,除了长子、矮子外,还有癞痢、麻子、跛子、瞎子。长子、矮子等带有骂人成分的称谓本身带有嘲笑愚弄的色彩:”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滑稽的逗笑、戏滤的调笑和无所顾忌的嘲笑是中国乡野村民生活状态的自然流露。是他们对乡村生活赋予他们幽默的天性与超然的野性的自然呈现。”在每一个民族文化的范围之内,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不同的幽默感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只有在乡村这一相对封闭而只向自身敞开的独立存在空间,只有在节日这一相对开放的特殊时段,村民们才能这样不拘形迹地娱乐狂欢,脱离了这一特殊的时间和空间,狂欢活动的功能和意义就发生了变异,自由的狂欢生存也不再有全面实现的可能。
“角色”的言语动作传达着幽默乐观的天性,”演员”的表演亲切而令人开心,”观众”、”演员”、”角色”又都是如此熟悉而亲昵,除了无所不在的戏剧性的”笑”,还能有什么呢?还有”闹”。”人越多越热闹”。长子、矮子、胖子、瘦子不仅带有愚弄嘲笑的色彩,更意味着人群的热闹与拥挤。”东也是灯,西也是灯,南也是灯,北也是灯,四面八方闹哄哄。”不仅人多,灯也多。人越多越热闹,灯越多越热闹,声音越大越热闹,这或许是为什么鞭炮总是中国传统热闹喜庆场景中必不可少的因素的主要原因。鞭炮与烟火分别代表着声与光营造的热闹气氛,因而官方虽屡禁而民间总不止。在乡村民间演出中,锣鼓又是必不可少的乐器。”锣鼓一响,戏就开场”。锣鼓传达的是粗质地的乐声,是与中国传统”雅乐”相对的”俗乐”,不仅俗,而且粗犷。清人徐珂对昆曲与皮黄戏作比较时说”大抵常人之情,喜动而恶静。昆剧以笛为主,而皮黄则大锣大鼓,五音杂奏。昆剧多雍容揖让之气,而皮黄则多《四杰村》、《八蜡庙》等跌打作也。”在欢快的锣鼓声中,王小六的妻子欢快地唱起了”开门调”:正(哪)月(呀)十(呀)五(哇)闹(哇)元宵,呀呀子哟,火炮(哇)连天门(哪)前闹,喂却喂却一喂却,喂却喂却我的郎呀,闹鼓闹嘈嘈(哇)。
这一段开门调总共有四十二个字,其中二十个字都是无实际意义的虚字与衬字,这些衬字与虚字穿插在有限的唱词中,节奏是快节奏,唱腔是欢音,衬字十分密集,唱词则稀疏,只为了突出一个”闹”。
我们再看《打猪草》陶金花唱词:小女子本姓陶,呀子咿子呀,天天打猪草,依呵呀昨天起晚了,哇呵啥,今天要赶早,呀子咿子呀,呀子咿,咿子呀呵啥,今天要赶早,呀子咿子呀。
这一段唱词只有四句:小女子本姓陶,天天打猪草,昨天起晚了,今天要赶早。由于由虚字和衬字组成的语气词的附着,使得原本简洁明了的唱词一场三叹。”呀子咿子呀”的唱腔与《闹花灯60嘿嘿,呀子一哈嘿嘿”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唱腔风格与调式,前者柔婉缠绵,后者粗犷豪放,与各自不同的唱词风格吻合。声音的重复使原本单调的唱词热闹起来,由虚字和衬字组成的咏叹在声音上传达的效果更甚于表情达意的效果,相同音节不断重复的反复咏叹仿佛是无边无际无拘无束的声音的狂欢。
同样是表达声音的狂欢,《打猪草》中精彩的”对花”却用了很少的虚字和衬字。”对花”形式来源于民间流行的男女对唱式情歌,而情歌实际上是情人之间悄悄话的声音化,声音化使情人之间秘密的私语公开化,因而不再具有有待遮蔽的隐私性,而具有向全民袒露的公共性。将秘密公开化使之具有公共性是娱乐狂欢的典型特征,声音在这里具有根本的本质性功能,声音的夸张与重复使声音传递狂欢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对花调”在声音上传达的效果也更甚于表情达意的效果。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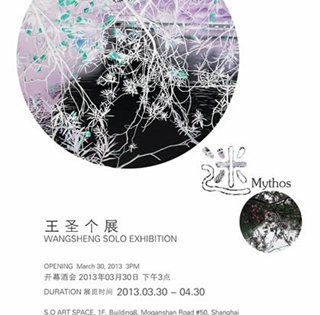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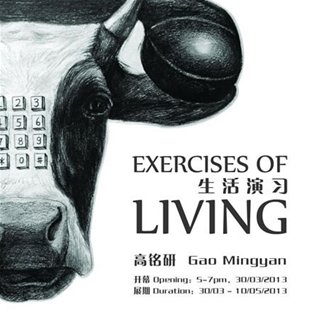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