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去年12月3日举办的北京保利公司2007秋季拍卖会夜场上,陈丹青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5天后,《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令人称奇的是,在4年前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牧羊人》仅以187万元成交,短短几年时间就猛涨了将近20倍,创下其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 画作不断卖出高价,陈丹青却在忙着出书。新书《与陈丹青交谈》(收集了陈丹2001年发表在《艺术世界》杂志上的12篇专栏文章)和《多余的素材》、《纽约琐记》两书修订本先后出版。不久前,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陈丹青的《退步集续编》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去年最受欢迎的图书,并成为多家媒体评选的年度十大好书。 如今的陈丹青,在很多人眼里已不是个画家,而是一个写书的作家。面对读者对其画家身份的质疑,陈丹青说,“我不必向外界证明我是画家。” 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力问题 笔者:从清华辞职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你都做了什么? 陈丹青:这一年我被邀请介入朋友的一个文艺项目,要弄到明年。时间搭进去不少。同时还在写写画画,还要编书,编书也花了好多时间。 笔者:清华大学这些年在重建人文学科,是不是它还没有完成一所综合型大学的准备? 陈丹青:综合大学的文科都是摆设。增系、增学科,能养很多人,申请不少钱,领导可以向上报:功能齐全了,就是这样。我目睹领导很想办好文科,但不知该怎么办。蔡元培擅自给陈独秀瞎编个学历,又把梁漱溟这样的愣小子请进来,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文科,什么是教育,现在怎么可能。 笔者:前段时间清华中文系的旷新年在博客上炮轰他们的系主任,后悔自己不应该到清华大学。 陈丹青:是吗?这种事每个系都有,张鸣炮轰领导,记者问我:“你对这事怎么看?”我说没什么看法,每个办公室门背后都在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几个特别不懂事的家伙会跳出来叫一下,有伤大雅,但绝对无伤大局。旷新年可能当真了,以为叫进去真的让你搞学术。就是个权力布置,布置完了,就可以了,然后别触犯权力,让权力正常运转,大家分摊利益,有饭吃。我谈了半天教育问题,等我离开后,发现我全错了。我不是在谈教育问题,也没有真的教育问题,都是权力问题,根子,是学术行政化。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常回国,也到中央美院代过课,当时的直觉就是——“解放前内行领导内行,解放后外行领导内行,近一二十年以来,外行就是内行,内行就是外行”。我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宁可退回到五六十年代,“外行领导内行 ”。 笔者:为什么? 陈丹青:那时的官员,真的是老粗,当兵的,他到业务单位——比方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文史部门——他不懂,他得靠业务人员,也就是现在说的专家学者出成绩,他的人格、身份,始终是“官”,他要贯彻意识形态,有时作风粗暴,遇到非常时期,他参与迫害文艺家,他自己也被迫害,但在相对正常时期,他不管你。现在呢,领导就是你同宿舍同学,他懂,你得顺着他,不然你走着瞧。 80年代开始提拔业务干部,初衷当然好,吸取历史教训,但演变到现在,很清楚:我宁可外行管我。文人当官,他不再是文人,而是干部,是上级,我们津津乐道什么学者官员之类,主语是“官员”啊。如果这官员人品不正,问题就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残了。这些年所有矛盾起于这一块。权力腐蚀人,他不会因为你是同行就善待你,你刺头?你不服?他细细地整你,名目多得是,我在学院多少老朋友,都跟我诉苦,苦不堪言,大致是“武大郎开店”,这滋味,大家都清楚,都知道。 笔者:所以教育问题到最后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陈丹青:我看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力问题。问题是它比赤裸裸的权力还可怕,因为一切是以学术的名义。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糟糕的办法,就是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有人再添了一句,经典极了,叫做“学术行政化,行政江湖化”。所谓“行政江湖化”,就是权力寻租,眼下每个领域都有权力寻租,不是吗? 在教育领域,最可怕的莫过这件事。你闹?你想走?你走吧,有的是人要进来,我这摊位归我管;你学术上反,你道德上反,好,慢慢收拾你,收拾的方式很简单,凉快你,一边儿去吧!我倒没遭遇这类窝囊,因为有点年龄资历,又完全没有行政职务的企图,对位子不构成威胁。但周围同事实在憋坏了。我还是选择走。我发现你跟他争,根本没用,你等于在争权力,不是争学术。 |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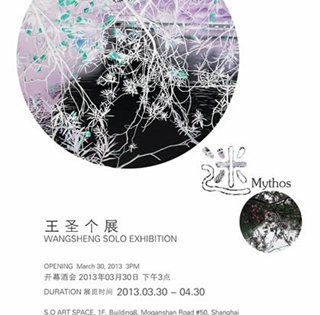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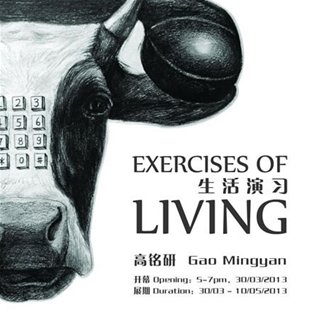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著名艺术
著名艺术 吴作人擅
吴作人擅 生命最后
生命最后 黄永玉:
黄永玉: 毕加索一
毕加索一 毕加索:大
毕加索:大 徐悲鸿挚
徐悲鸿挚 林风眠:
林风眠: 画与诗 访
画与诗 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