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戏曲改良运动之后,一场来势猛烈的新文化运动悄然兴起。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大力提倡白话文。2月1日,陈独秀支持胡适的主张,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一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为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又认为“文学当以宇宙、人生、社会为构想对象,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以白话文为文乃天经地义之事。”接着,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表示支持。于是,文学革命就由几个留美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从此,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文学革命的主旨是要推翻旧文学。戏曲作为沉积七百余年的艺术,自然不能幸免。1917年3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寄陈独秀》,支持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并严厉剖析戏曲之弊病,首次从根本上对戏曲发难。他认为,京剧缺乏理想,文章不通,称不上是戏剧。说中国旧戏重唱,且脸谱离奇、舞台设备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指出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拙劣恶滥”。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主张戏曲要用当代方言,以白描笔墨为之,改良发展皮黄戏,昆剧应当退居。在这种针对戏曲艺术的激进言辞躁起之时,熟悉戏曲艺术的人士开始为戏曲辩护。1918年,张聊公(张厚载)发表《民六戏界之回顾》,盛赞梅兰芳古装新戏,大谈昆剧之复兴。同年12月1日,《春柳》杂志在天津创刊,天鬻子在《春柳》第1年第1期发表《昆曲一夕谈》,认为昆曲“于中国现今歌乐中,为最高尚优美之音”,提倡振兴昆曲。面对给戏曲的辩护,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士也不甘示弱。于是,在1918年,两派文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就戏曲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认为西方文学方法比中国文学要“高明”和“完备”,蔑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6月15日,张聊公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反驳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的戏剧观,认为要对旧戏进行改良,必须“以近事实而远理想”,反对理论空谈。同期“通讯”栏发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的辩论文章,认为中国旧戏的脸谱和武打均为“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中国旧戏“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中国要有真戏,“自然是西洋派的戏,决不是那'脸谱'派的戏”,主张要把旧戏“全数扫除,尽情推翻”,以便推行“真戏”。1918年10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发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认为戏曲应当废去乐曲、脸谱、把子等“遗形物”,强调只有采用西方近百年来的戏剧新观念、新方法,中国的戏剧改良才有希望。同期《新青年》还刊发傅斯年的《予之戏剧改良观》、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和张豂子的《我的中国旧剧观》。傅斯年认为,中国戏曲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欧阳予倩认为,中国旧戏从来没有剧本文学,是无本之木,提倡向西方学习,创设剧本,建立剧评、剧论,培养演剧人才。面对这种言论,张豂子认为,“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拿现在的社会情形看来,恐怕旧戏的精神,终究是不能破坏或消灭的了”。
如果说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起的戏曲改良运动对戏曲的批评还十分温和,还指望在旧剧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话,那么进入1917年,由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文学革命的激进派文人对于戏曲则是全盘否定。这种态度是直接与激进派文人期望用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的动机相联系的。同时,还与他们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顽固残忍的激愤情绪有关。他们从剧本到表现形式全方位地否定戏曲,就是要打碎支撑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封建文化的一个部分。但由于对戏曲认识的过分情绪化,就引起了张厚载、天鬻子等人对戏曲的辩护。他们从戏曲艺术的客观实际出发,阐明戏曲艺术的特性,力图在客观阐述的过程中回击对戏曲艺术的情绪化攻击。从20世纪戏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显然张厚载等人的观点更为客观冷静一些。在这场争论中,有一位从戏曲改良运动中走过来的重要人物,那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在戏曲改良运动中仅是从局部指出戏曲应当改进的地方,反对戏曲中的“神仙鬼怪戏”、“淫戏”和“富贵功名的俗套”,但对戏曲的社会功能还是大力渲染铺张,主张利用戏曲宣传改良;而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他却急速转向对戏曲的全盘否定,这首先与戏曲改良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其次与他对这次中国文人准备全力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动机持赞同态度有密切关系。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持续两年的关于旧剧的争论,是进入20世纪以来继戏曲改良运动之后中西文化在戏曲艺术上的第二次交锋。这次交锋虽然在程度上比前一次更加剧烈,但因参加者纯属纸上谈兵,没有人亲自投入到戏曲艺术实践中去,对于远离争论的戏曲艺人而言没有多大影响,戏曲仍然在艺人的实践中发展着。这次争论有两方面的重要成绩,一是对最先自日本引入、正在成长的西方话剧在中国的扎根从舆论上起到了维护作用,西方戏剧写实观念在这种舆论中被加强,对戏曲在写实观念上的滋长具有刺激作用;二是在对戏曲的辩护中引起中国文人对戏曲艺术自身特点的思考。此后,中国舞台上,一方面活跃着戏剧舶来品--话剧,另一方面戏曲艺术仍然占据大多数舞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政治上的论战淹没了对戏曲艺术的论争。持续两年的关于戏曲艺术的争论宣告停歇。就在这时,梅兰芳首次率团赴日本演出(1919年4月21日至5月27日),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天女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虹霓关》、《贵妃醉酒》等,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中国戏曲首次在国外正式亮相。日本人对戏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评论界,对梅兰芳的演出发表了兴趣盎然的议论。神田在《品梅记》中说:“我这次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作为象征主义的艺术,没有想到它卓越得令我十分惊讶。中国戏剧不用幕,而且完全不用布景。它跟日本戏剧不一样,不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只用简朴的桌椅。这是中国戏剧非常发展的地方。如果有人对此感到不足,那就是说他到底没有欣赏艺术的资格。……使用布景和道具绝对不是戏剧的进步,却意味着看戏的观众脑子迟钝。”对于梅兰芳的表演,日本人士同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丰冈圭资在《品梅记》中称赞梅氏:“嗓音玲珑剔透,音质和音量都很突出。据说这是他有天赋之才,再加上锻炼的结果。但他的嗓音始终如一,连一点儿凝滞枯涩也没有,而且同音乐配合得相当和谐,有一种使听众感到悦耳的本领,真令人不胜佩服。”洪洋盒在《品梅记》中赞叹梅氏演出《天女散花》的舞姿:“步子、腰身、手势都很纤柔细腻,蹁跹地走路的场面很自然,人们看到这个地方只觉得天女走在云端,不禁感叹梅氏的技艺真是天斧神工。”梅兰芳的赴日演出不仅引起日本人士的赞叹,而且也令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当年的《春柳》杂志载文说:“甲午后,日本人心目中,未尝知有中国文明,每每发为言论,亦多轻侮之词。至于中国之美术,则更无所见闻。……今番兰芳等前去,以演剧而为指导,现身说法,俾知中国文明于万一。”梅兰芳赴日演出的成功,对于1917、1918年中国激进派文人对戏曲的攻讦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回击。从此,中国人开始较为平和地看待自己的艺术。这种平和态度在20年代的国剧运动中已流露出来。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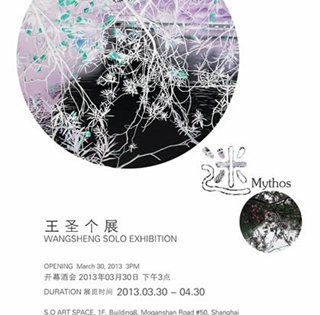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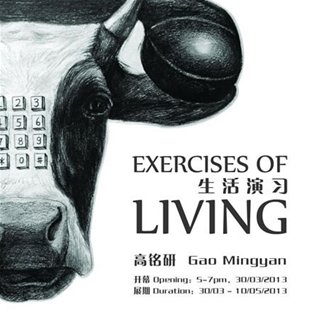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