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 北京西单商场
蔡焕松:他们对影像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的认知比我们早得多。

王文澜:比如说北京第一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的开业,我只拍了剪彩就完事了。但是刘香成把这当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让外资老板坐在建国饭店前,用广角拍下来,作品取名《孤岛》,意思是这个饭店是处在社会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资本主义孤岛;还有故宫前面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小伙子挥舞着玻璃瓶的可口可乐,说明西方文化到了中国的皇城,这种玻璃瓶的可乐现在已经没了;北海白塔前的两个少女戴着的墨镜上贴着商标,那是一个时尚标志,当时被戏称为“白内障”……这些生活细节,都躲不过他的镜头。
而这些我都经历了,但是毫无感觉。摄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人家拍了,你没拍,就说明你不行,就这么简单。你把一个作家、画家关上十年,出来他还可以写、可以画。你把摄影家关十年就废了,摄影语言是很易碎的,是过期作废的。所以我平常要战战兢兢、像维护水晶一样地去维护眼光的力度和锐度,思路要清晰,视觉要清楚。
蔡焕松:你摄影理念的彻底转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王文澜:我从80年代就经常算一笔账,我虽然错过了文革的拍摄,但从1976年开始拍到2000年,这是1/4世纪,如果活到2025年,我就能拍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50年。有些人说他那个地方没什么拍的,怎么可能没得拍?就算拍你的孩子也能出一本书了,多么好的一本书。还可以拍自己的爱人、家庭、学校、工厂,或者你家附近的一个急诊室,你盯着拍三年就了不得,这就是社会的变化。摄影就是要表现那些即将产生和消失的东西。
蔡焕松:基于这种种考虑,你就开始拍摄你的《自行车王国》等系列。
王文澜:自行车很早就拍过,但没想形成系列。后来到了《中国日报》,每天骑着车上下班,觉得离不开自行车。中国是自行车王国,每个城市的自行车都是流动的长城,我想自行车肯定会越来越多,多么丰富的题材,够我拍很多年了。可没想到自行车现在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外国有好几个摄制组看了我的照片,问我在哪儿还能拍到这么多自行车的镜头?我说再也找不到了,没了!这反过来也证明,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从两个轮子到了四个轮子,那些关于自行车的镜头就成了永远的记忆。
蔡焕松:你当时的初衷就是记录浩浩荡荡的车流,并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你的主观愿望是这样,但客观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你原本拍摄认为会更快发展的自行车,却成了留存即将消失的一种中国人原本无法离开的交通工具的影像。这批影像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成了未完成的瞬间,产生了与你拍摄动机相反的效果。你后来还拍了北京的胡同系列。
王文澜:胡同也是越拍越少,拍它的孤独、它的无奈,原来的三千条胡同随着城墙的拆除被慢慢蚕食,变成了现在的几百条。2000年后,拆的速度比拍的速度还快。只有摄影能够把这段记忆保留下来。
蔡焕松:你还拍了很多人物。
王文澜:环境肖像比较多。由于工作关系,接触不少名人,觉得环境肖像也是一个种类。同时我又拍了更多的百姓肖像。现在回头看看,通过人物反映30年的历史进程也能形成一种印记。
原来我对图片中的文字很不认可,我的照片也很少用文字说明,最多写上时间地点。后来我发现有些画面中的文字反映了历史的痕迹,就专门把它作为一个符号系列,可拍的东西真是很多。
蔡焕松:我们长期以来的影像评判标准,是站在当下的诉求而制定标准来衡量作品,甚至那些影像的标准受时代制约,这是错误的。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个评判标准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我研究了你的影像个案后发现,你经常当评委,整个潮流和标准你最清楚,但是你一直没有大的改变,换句话说你完全有条件、有机会依据当下的评判标准,去随波逐流拿个大奖,但你固守着自己的执著,追求着原本的瞬间、有意义的切片或称碎片,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王文澜:摄影确实有很功利的一面。所谓功利无非就是拿这个照相机得到什么?有人是拿着照相机玩儿,就像我一开始那样,玩儿也是一种追求;还有一种是炫耀心理——我的照相机挺棒、挺高级;另一种是要玩儿出名堂,名堂就是堂上之名,到处投稿,到处拿奖。
当年我也投稿,也参赛。那会儿在部队,拿双镜头反光相机加上近摄镜拍的麦穗和落日叠加起来,起名叫《眸与睫》。那时拍照片就想得到证明,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就是要获奖。经常研究是哪家举办的比赛,评委是谁?投其所好,投稿就是迎合,因为目的是获奖,不迎合就很难拿奖。
后来慢慢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很多摄影者什么奖也没得过,但他的影响很大;他不参展,却能得到整个业界的承认。因为他的观察是独到的,作品有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摄影价值的判断。摄影比赛只是一个活动,就算搞得天大也是一样,得了金牌只是一时的收获。我觉得摄影之所以没被其他艺术门类所代替,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记录历史的功能。为什么那些老照片能够让人叹为观止?因为摄影是讲年头的事,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我以前也有急功近利的时候,现在安静多了,拍到有用的东西总会用得上。
蔡焕松:换句话说你的底线是不变的,只要记录下来是真实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价值依然存在。但是当下的评判标准由话语权来界定,这个话语权在谁手里,制定的标准可能就不一样,影像的评判结果自然也不一样,大家习惯以得奖论英雄!
王文澜:这些年是俗文化流行,努力挣扎也难于免俗。主要看你把这些追求放到创作中的什么位置上,你的独立空间保留得越大,你的艺术收获越深。每个影展比赛都有各自的话语体系,拿摄影节来说,平遥的和连州的就不一样,两边来的人都挺有分量,但展出的照片却不一样,这反映了创作的多样性。在北京我有机会就去逛宋庄、798、草场地,就是想从这些不同风格中开阔思路。我也想改变,但在按下快门的时候有时难免还是老套路。
蔡焕松:摄影界一直有人把你和贺延光并称为新闻摄影的双子星,并以此衡量你们在中国新闻改革进程中各自在所属报纸上所发挥的作用。你跟贺延光有很大不同,他拍的很多作品都与当下靠得特别紧,而且有些则成为该亊件标志性的作品,但你恰恰走了另外一条路。据我了解你俩对新闻摄影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具体到每个人的理念尚有差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王文澜:我认为中国原来的新闻摄影是名不副实,应该称作宣传摄影。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步遵循新闻规律去摄影报道。贺延光在《中国青年报》,他的思想敏锐度、新闻嗅觉度都很强。但我似乎更应该从事画报杂志这样的工作,因为我拍完东西后并不急于发稿。有些人问我不发表干吗,都捂馊了?这可能是性格使然,我就是喜欢闷着。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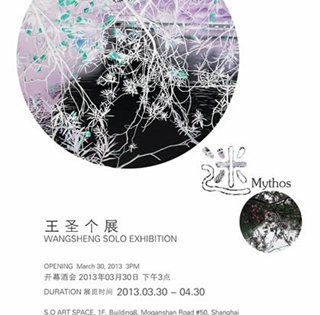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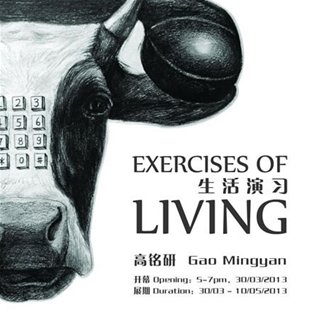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美联社首
美联社首 为了未完
为了未完 柯达专业
柯达专业 时尚摄影
时尚摄影 让.鲍德里
让.鲍德里 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 汤普森 时
汤普森 时 雪江游艇
雪江游艇 柯錫杰
柯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