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上海城隍庙
蔡焕松:你是不是觉得捂一捂、沉淀一下拿出来会更好?
王文澜:我喜欢这种讲年头的感觉。贺延光是急的,我是慢的;他是直的,我是曲的;他是实的,我是虚的。比如同样拍非典,他快速反应地跑到地坛医院了,而我则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是另一种表现方式。后来我和贺延光开玩笑说,你是敢于斗争,我是善于斗争,一对哼哈二将。
蔡焕松:你跟贺延光之间都很理智,摄影目标又很清晰,事实上应该是竞争对手?
王文澜:同行是冤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俩还老爱往一块儿凑,见了面就掐——打嘴仗,唇枪舌剑,旁边的人看着都乐。尽管拍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拍出来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怕去同一个地方。他拍的东西我会认真去看,我拍的东西他也很关注,我们都心中有数。我们常在一起吃喝,但不是酒肉朋友。听说《中国摄影家》想摆一个擂台让我们“PK”,我们俩都盼着呢。
蔡焕松:贺延光的东西往往比较直接、激烈;你的影像则温和委婉,你喜欢慢慢地诉说。你拍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这些也是急的,那是偶然的激情释放,是特殊情况。但我老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探讨评判标准和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的研判在若干年后会发生变化。当年拍宣传图片的时候没感觉会错,我们都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封面当标准、作模式,当年全国影展的评判标准也是照那个标准定的。由此我联想到你的“未完成瞬间”,觉得挺深的。
王文澜:没什么深的,就像一条蚯蚓,只是有点钻劲,是有弯度。当你觉得自己的摄影是在观察与评判社会,可以用摄影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摄影才是有意义的。
蔡焕松:你把影像定在历史的高度上,所以就觉得永远未完成。
王文澜:虽然是历史的高度,但历史是由很多细微的切片积累构成,所以任何小题材、小人物我都不放过。
蔡焕松:长期以来很多摄影记者都特别留意具有特权的影像,因为有些新闻和人物需有特权才能拍到。但我看你倒是很不在意。
王文澜:那些内容固然重要,有机会去拍也很好。但如果头脑僵化,很可能就浪费了那个机会。新华社的姚大伟则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给我们留下了温总理很多平易近人的瞬间。
蔡焕松:你好像并不特别重视这些事儿?
王文澜:因为在摄影史上很多著名作品并不都是出自特殊的场合,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极小部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平淡的生活。衣食住行里有很多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你抓住了那些凡人小事就会成为你的代表作。
蔡焕松:现在很多人的器材装备越来越厉害,像素也越用越高。你却把小型照相机用得得心应手,有什么使用心得?
王文澜:相机的使用适得其所最好。我一般机不离身,小型相机揣在兜里比较方便,能迅速地接近拍摄对象而不易被其察觉,不易引起他人的反感,没必要老拿个大家伙吓唬人。但也有很多任务需要大相机,比如拍中央新闻、体育新闻。我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小型相机拍摄报纸头版的照片,成像质量很好,在没有限制的场合,小相机不会引起被摄对象的注意。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着对摄影器材的使用,那就是面子,觉得手里拿着好机器很气派,这多少对自己不太自信。
最早我出去采访也会带几个镜头,后来我发现很多时间都用来琢磨怎么换镜头,老在想用哪个镜头更理想。后来换镜头的事儿我不干了,这样就能很专心地琢磨如何去拍。当然我现在也使用胶片机,它是一种承载信息的固有方式,这个方式让我觉得踏实。数码存储的空间总让人有种莫名的担心,所以两条腿走路。
蔡焕松:有人说你是中国摄影界的“四不像”——不像新闻记者,不像纪实摄影,不像玩艺术的,又不像搞当代的。你究竟想干吗?
王文澜:“四不像”在生命遗传链中是有独特位置的,只不过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所谓纯种罢了。但杂交更具兼容性。
蔡焕松:也就是说你承认这种“四不像”风格?
王文澜:我觉得当代啊、前卫啊,它不像美术,不像摄影,但像艺术,都是处在一种边缘状态,这种状态比较从容,有余地。五谷杂粮,营养丰富,即使是另类也挺好。
蔡焕松:那么你觉得靠哪类多一点?
王文澜:我想用一切手段在瞬间中进行融合。我尽可能多地关心社会的方方面面: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要反映半个世纪跨度的历史进程。原来我对经济没有兴趣,现在也接触金融、房地产的知识,因为这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还有互联网上的内容,我从儿子身上知道他们这代人的兴趣,实际上他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根本进不去,但也要了解。只有这样,你的摄影才能反映新世纪的变化。
蔡焕松:你是想通过努力,在社会中找出一些生活细节,碰撞出偶然性的瞬间,用这些碎片来储存、编辑半个世纪的进程。因为我看你并没有尽力去抓大题材,而是用生活中偶然性很强又很难得的瞬间来讲述故事。
王文澜: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不动声色。当然碰上了大题材也要参与,但基本上是以日常生活为主。
蔡焕松:然后用众多有含义的普通事件构成一个大的乐章。
现在一些场合上,包括一些大活动,新闻记者大概有两种拍摄状态:一是用马达连拍,片海战术,拍了回去挑;二是拍一张是一张,讲质不求量。你对这两种拍摄方法怎么看?
王文澜:首先我不喜欢闪光灯,尽管原来也用过,却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我现在肯定不用。因为有了数码的宽容度,不用闪光灯完全可以满足低照度拍摄的需要,除非是商业摄影。至于马达,对中央新闻、体育摄影、突发事件是有用的,日常摄影没必要依靠它。
蔡焕松:马达声、闪光灯可以制造气氛。
王文澜:现在提倡低碳生活,摄影也要讲低碳方式。马达、闪光灯,费卡费电,也是一种能源浪费,不是低碳拍摄。另外拍得越多,删起来也费劲。
蔡焕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拍摄者对自己捕捉的这个瞬间底气不足,怕抓不住,拍不好。
王文澜:摄影就是瞬间语言,快门之间决定成败。你要拍好一个组照,你必须面对单张照片的挑战。拍好独幅照片是每个摄影者的首要目的,如果你在一张照片里都说不清楚,你也把握不了一个组照。如果你对瞬间没有信心,你就去拿摄像机吧。每个从事摄影的人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拍摄观念。我原来特别关心摄影的技术、技巧,随着器材的自动化,更加关注摄影以外的东西,关注一切和生活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在某一时刻,通过你手指的瞬间释放,回到了摄影层面。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变化!
蔡焕松:关于“未完成瞬间”的话题,现在是否可以这样定义,你把一生对摄影的追求当成一部作品,迄今拍摄的只是这部未完成作品中的些许时空切片,影像未完成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留给社会和历史去评判?
王文澜: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未完成的状态上,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事件,都包罗在一个大的历史题材里。这么大的题材,到哪儿才能算一站,怎样才算是拍完了呢?我要做的就是呈现一个摄影者的独特观看,力求在中国历史发展巨变的宏大交响乐中,演奏好自己的乐章。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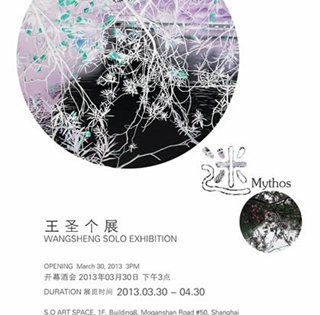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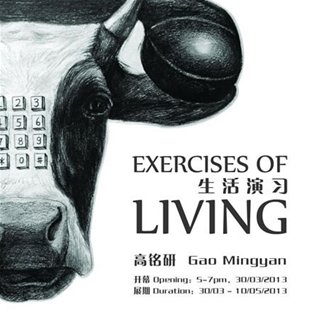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美联社首
美联社首 为了未完
为了未完 柯达专业
柯达专业 时尚摄影
时尚摄影 让.鲍德里
让.鲍德里 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 汤普森 时
汤普森 时 雪江游艇
雪江游艇 柯錫杰
柯錫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