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是一代文学成就的体现,也是元代语言研究的最直接依据。对元杂剧语言的研究不但是语言训诂者的重要课题,更对戏曲语言的借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数年来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过若干戏曲辞语训释方面的拙文,今欲就元杂剧词语运用中的某些共性倾向作一综合性探究,以期寻求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一、 元剧中方言土语的普遍性
元杂剧中的方言土语应用得相当普遍,通过我们的综合考察,发现这些方言土语几乎全是北方方言和土语,其中绝大部分在当今北方地区还能寻到它们的原形或嬗变形式。如:《王粲登楼》第一折:”放鱼的子产,磕他怎的?”《曲江池》第三折:”你嗓嗑他怎的?”《忍字记》第一折:”他嗓嗑贫僧哩。”以上三例中的”嗑”、”嗓嗑”,义为没好气的责怪、呵斥,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动词。现今河北、山东一带民间口语中还有大量的应用。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将其解释为”讥笑”,显然不符合本词原意。
《任风子》第三折:”这手帕做布,好做铺尺。”《诈妮子》第二折:”剪了靴檐,染了鞋面,做铺持。”《杀狗劝夫》第二折:”将一条旧褡扯做了旗面,将一领破布衫做了铺迟。”以上三例中的”铺尺”、”铺持”、”铺迟”实际上是一个词,属于最典型的河北、山东地方土语词,它的规范写法究竟应该如何,至今无法确定,但这个词语却仍旧在广泛地使用。它的意义应该是做衣裳裁剩下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碎布或旧得不能再穿的破衣服、破布条。旧时人们将这些废料收集起来,用面浆把它们层层粘住。打成袼褙,用来做鞋帮或纳鞋底,也有用来做抹布的。《戏曲语词汇释》将其归纳为”抹布”,显然不全面。
《射柳捶丸》第三折:”把都儿,与我摆开阵势。”《老君堂》楔子:”巴都儿来报,大王呼唤,不知有何将令。”以上二例中的”把都儿”、”巴都儿”都是蒙古语的音译,义为”壮士”、”英雄”等。至今此义还在蒙古语中频频出现,甚至有不少蒙古族人以此为孩子取名,不过现在这个词一般写作”巴图”、”巴图鲁”、”巴图拉”等,不再写作”巴都儿”。
《陈州粜米》第二折。”我须是笔尖上挣来的千钟禄,你可甚剑锋头搏换来的万户侯。”《西厢记》四之三:”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汉宫秋》楔子:”俺祖高皇帝奋布衣,起丰沛,灭秦屠项,挣下这等基业。”以上三例中”挣”、”挣揣”和”挣”是意义相同的三个词,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挣”字的意义具有普遍性,如今所说”挣钱”、”挣口饭吃”,没有人会感到难懂,而换成”挣”、”挣揣”,到了江南地区,人们就会感到不知所云。所以《戏曲语词汇释》将其解释为”挣扎”,显然乖违原义。
《秋胡戏妻》第二折:”媳妇儿怎敢是敦葫芦摔马杓。奶奶也,谁有那闲钱来补笊篱。”《李逵负荆》第三折:”打这老子没肚皮揽泻药,偏不的我敦葫芦摔马杓。”以上二例中的”葫芦”指北方人从缸里舀水的瓢,”马杓”则是”葫芦”的别名,也就是说,此种日用品,今河北、山东一带人既常称之为葫芦,又常称之为马杓。
这几组例子可以说明,京、津、冀、鲁一带的方言土语以及某些蒙语译音词在元剧的道白及唱曲中用得十分广泛,而在南方,尤其是江淮以南地区的方言土语中则完全见不到,这是因为元代首都在大都,其文化当然也是以大都为中心,而大都居民的组成,除蒙古人外,主要是其附近的河北、山东二省人。元剧是一种以语言为主的艺术形式,它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大都,并由大都向附近的冀、晋、鲁、豫等地扩散。
以北方方言为主的戏剧、说唱,长时期内并没有扩展到江淮以畔,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是北方的地方戏曲,它与南戏逐渐形成南北共荣的局面。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考证,杂剧作家绝大部分是京、冀、鲁、辽东以及西域人,其间虽然也有个别江南人,但这些人又都是长期游于大都,深受北方文化及语言的影响。同时我们又发现,这些江南人大多只写散曲而不写杂剧,而散曲不过是文士案头之物。它的社会功能与杂剧迥异,就便是散曲作者,其江南人与北方人的遣词用语也多有不同,南人散曲趋雅,而北人散曲趋俗,造成这种雅俗之分,方言土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元剧中的衬字与虚字
元剧中的衬字与虚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所谓衬字,指曲牌规定每句固定字数之外多馀出来的一个或几个字。如《气英布》第一折《玉花秋》曲:”势到来如之奈何、若是楚国大臣见了呵,其实难回避,怎收撮?”根据《玉花秋》的曲牌,这几句的格式当是”平平仄仄平(韵),平平仄,仄平平(韵)”,据此可见,以上首句中的”势到来”、次句中的”若是”、三句中的”其实”是作者写曲时临时加入的部分,这些部分就叫衬字。所谓虚字,是指无具体意义的某些形容词、语气词、象声词,它未必是衬字,如上例首句之”奈何”、次句之”了呵”、三句之”其实”,则属于虚字。我们在这一节中之所以把衬字和虚字放在一起来讨论,是因为元剧中的这两类词语运用,除了南北方共同使用的”了”、”呵”等之外,大部分具有明显的北方地域性,也就是说,元剧中的虚字或衬字,只有在北方作者笔下才大量出现,这也说明元杂剧是深受地域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如:《僧尼共犯》第二折:”慌得地两头儿低羞笃速,唬的地两眼儿提溜秃卢。”《降桑椹》第一折:”看他两个眼剔留秃鲁的,他真是个贼。”《病刘千》第二折:”横里五尺,竖里一丈,剔留秃,恰似个西瓜模样。”以上三句中的”提溜秃卢”、”剔留秃鲁”、”剔留秃”均是京冀地区人形容圆物乱滚的样子,前两句是说人的眼珠乱转,第三句是说西瓜滚动,尽管词形很不统一,但作为一个带地方色彩的虚字,只要是在这一地区,单凭这几个音节,听说听唱的人便知是什么意思。
《两世姻缘》第一折:”对门间壁,都有些酸辣气味,只是俺一家儿淡不刺的。”《举案齐眉》第三折:”恰捧着个破不刺碗内,呷了些淡不淡白粥。”《五侯宴》第四折:”你那里干支刺的陪笑卖查梨,不须咱道破他早知。”《张生煮海》第三折:”秀才家能软款,会安详,怎做这般热忽刺的勾当?”以上四例中的”淡不刺”,即平淡;”破不刺”,即破;”不刺”属语助类虚字,没有实义。”干支刺”,即干,”支刺”也是语助。”热忽刺”,即滚烫、热烈,”忽刺”与”不刺”、”支刺”作用均同。至今京津地区口语中,”不刺”、”忽刺”一类的语助词还在广泛地用着,可证这类虚字在北方地区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东篱赏菊》第二折:”如今选将这个陶老爷来,好个撇古东西。”《生金阁》第二折:”我这夫人有些撇拗,嬷嬷,你须放出那蒯通般舌来才好。”《昊天塔》第二折:”我想孟良是个撇强的性儿,你使他去,他可不去。”以上三例中的”撇古”、”撇拗”、”撇强”都是性格古怪的意思,而这个主要意思又是由”撇”(即今北方话中”别扭”的”别”义)来表示的,今北方口语中仍有”这个人真撇(别)”、”不要跟他撇(别)”的说法。这样一分析,上面三词中的”古”、”拗”、”强”要么属于词尾(如”古”),要么与”撇”构成同义复合词(如“拗”、”强”),广义来说,都属虚字范畴。
类似带有浓重地方区域性的衬字和虚字在元剧中不胜枚举,这说明元剧作者在创作思想上有着一种努力适应民众口味的特点。不难想象,如果元剧中的唱词和道白都是些古奥词语,普通百姓怎能对它发生兴趣?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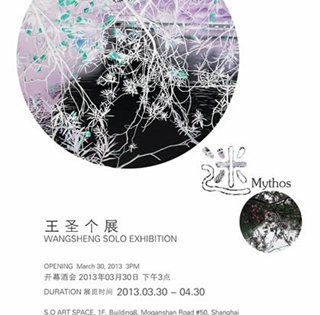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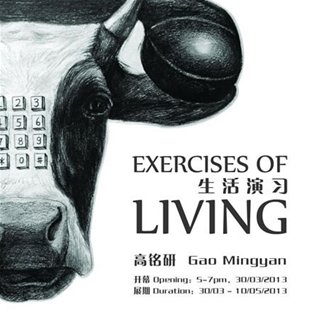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