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元剧中的典故应用
运用典故是汉语实践中重要的修辞手段。所谓典故,即将一个精辟的故事(或具有故事性的人物)浓缩成几个字,用在句子当中。这样做既扩大了语言的容量,又体现出作家较高的文学素养,如”四面楚歌”,就是一个成语典故,表面上看起来只有四个字,但它所包含的是一个英雄末路的复杂历史事件,读者看到这四个字,便会联想到一代豪杰项羽兵败途穷,被刘邦围困在乌江岸边的悲壮场面,甚至能联想到黑夜中士兵们咿咿呀呀的凄凉歌声,达到了很强的修辞效果。正因为如此,历来文人们都很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这类特殊词语,南北朝后的文学家写诗作赋,用典几乎成为定式,衍至唐宋诗赋,典故越用越多,谁能多用典,谁能用僻典,在一定意义上竟成为衡量作品优劣的尺码。当然,也有不少清醒的作家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认为堆砌典故是迷失了文学的本原。元杂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出自文人之手,当然不可能与用典无关。同时元杂剧又有它自身的特征,这种说唱合一的特殊文学形式,它的受众是最广大民众,这些人中固然也有知识分子,也有粗通文墨的秀才学究,然而更多的则是没有什么文学修养的平民阶层,这就要求杂剧作家在写作时要使自己的剧本尽量大众化,口语化,同时又不能太失文学魅力,只有掌握好这个尺度,才能写出受人欢迎的好戏。这个尺度如何把握呢?我们发现,元曲作者对典故的使用约定俗成地遵循了这样几个原则,一、典故还在普遍地运用,因为它是汉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二、尽量少用典故,避免堆砌之嫌。三、尽量选用熟典和普通典故,尤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熟典,以满足低水平人群的欣赏口味。四、用俗典增加生活气息,使戏剧更贴近民众生活。如:《东坡梦》第一折:”这雪山中不比巫山梦断魂,那里有暮雨朝云?”《城南柳》第二折:”恰便似汉刘郎误访桃源洞,奈惜花人有信难通。”《梅香》楔子:”合着俺三移的孟母,应对不尘俗。”《忍字记》第三折:”我识破这红尘战白蚁,都做了一枕梦黄粱。”《青衫泪》第三折:”我则道是听琴钟子期,错猜做待月张君瑞。又不是归湖的越范蠡,却原来是遭贬的白居易。”翻阅元剧,此类既雅且俗、妇孺皆知的典故触目皆是。读这样的句子,听这样的戏文,会使人感到既有文采,又能领悟其中深意,这说明元杂剧的用典恰到好处。”巫山”、”云雨”出自战国宋玉《对楚王问》,是流传千古的佳篇。”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凡旷难怨女动情时,很自然会想到这个故事。有时作家还把典故有意铺陈开来,使意趣更浓更深,如《倩女离魂》楔子:”他是个矫帽轻衫小小郎,我是个绣帔香车楚楚娘。恰才貌正相当。俺娘向阳台路上,高筑起一堵雨云墙。可待要隔断巫山窈窕娘,怨女鳏男各自伤。”其实作者铺排这许多文字,只是借巫山云雨的故事来表现少女思春的热烈与焦灼。与此相类的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神女于桃花开时,出自《太平广记》卷六十一《天台二女》,后来”天台”、”桃源”就成了梦求佳丽的代称。为教育好子女而三迁的孟母,出自汉刘向的《列女传》。表示富贵荣华如大梦一场的黄粱梦,出自唐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
他如《列子》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待月西厢下、《国语》中的范蠡功成身退游五湖、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不仅一般人耳熟能详,就是不识字的人,也口耳相传地了解过这些故事。可以设想,如果元杂剧写得像宋朝《西昆酬唱》那样用典晦涩,它同样不可能拥有广大的受众。从以上诸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规律:这些典故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除了它们本身具有动人之处外,又往往是人们普遍会亲历的某些感情或极具社会意义的某类现象,比如爱情爱欲,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追求。又如孟母三迁,代表着一种伟大的母爱。黄粱一梦,代表着人们对物欲追求的理性反思。伯牙摔琴谢知音、同是天涯沦落人,代表着人们对纯真、和谐友情的渴望。范蠡功成游五湖,则代表着对统治阶级残暴本质的认知。元代的剧作家们无疑都是想通过戏剧这种载体完成自己对社会的评判,对美好的歌颂和对丑恶的鞭挞,而不是把戏剧当作案头古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自然懂得在自己满腹才学中拣选出最易懂又最具哲理性的简单典故用在创作中。元杂剧虽然是几百年前的作品,但今天稍有文学功底的北方人,读起来都不会感到语言上有大多障碍,应该说,这与当时作家们看似无心却甚有心的词语运用有很重要的关系。
四、 元剧语言中的民俗色彩
元杂剧语言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量吸取民俗文化的内容。在元剧中。我们感觉不到有什么语言规范,也感觉不到有什么选词用语的禁忌,不论作者演绎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都采用了反映当时大众心态的表献方式,这种方式包括若干方面,如服装、音乐、布景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语言,因为语言是整出戏剧的灵魂,这个灵魂如果不能做到与民众心理相通,则变成了死灵魂。当时的作家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剧目中,都是说家常话,家常到能使观众与台上的演员进行角色置换。”演绎古人的故事,说当今百姓的话语”,台上台下在时间、空间上都没有了距离。中国的民俗内容十分广博,这些民俗又可以用语言形象地表达出来。戏曲语言中充满了民俗的内容,就能更显示它的民族性和根植于民众内心的文化内涵。举例来看:《张生煮海》第四折:”我和你同会西池见圣母。秀才也,抵多少跳龙门应举,攀仙桂步蟾蜍。”《忍字记》第一折:”我见他磨损乌龙角,他那里笔蘸一管紫霜毫。我只见刃字分明把一个心字挑,他道这忍字是我随家宝。巧言不如直道,我谢你个达磨来把衣钵亲交。”《冤家债主》第四折:”一灵儿监押见阎君,闪的我虚飘飘有家难奔。明知道空撒手,怕什么业随身。托赖着阴府灵神,得见俺那阳世间的儿孙。”《桃花女》第三折:”别人家聘女求妻,也索是两家门对。写婚书要立官媒,下花红,送羊酒,都选个良辰吉日。……你在那《周易》内显神通,怎如我六壬中识详细。”例1中先说到瑶池西王母,这是中国神话中神仙的代表。所谓”同会西池见圣母”,就是说双双去做神仙。神仙思想是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代表了汉民族祖先希望摆脱尘世羁绊进入到自如世界的一种企盼,属于共性的民族心态。观众听到这个简单的词语,很自然会联想到碧落琼瑶的神仙境界。其下又说到”跳龙门”、”攀仙桂”,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宦之途的代称。中国自古以来以官为贵,人人希望当贵人,这也是一种共性民族心理。尽管这里用了比喻,但说出来谁都懂,不仅能理解字面的意义,更能透过字面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层次意义。例2这段话前半部分讲的是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刃字分明把一个心字挑”,是说人受到委屈,就如同用刀戳心,不能容忍,有仇必报,有冤必伸,”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代表了国民性格中刚强豪侠的一面。”他道是忍字是我随身宝”,是说遇事能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退一步天地宽”、”小不忍则乱大谋”、”吃亏是福”,代表了国民性格中柔韧的一面。不论是豪侠还是柔韧,也不论二者孰优孰劣,总之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共有的心理形态。后一句”达磨来把衣钵亲交”,则是借用佛教衣钵相传的传统形式来表示聆教受益。很多人认为佛教是舶来品,不能代表国民心理,其实不然,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百年间并无多人问津,后来还是借助了中国玄学,才得以大倡其道。应该说,中土的佛教是一种被汉民族同化了的宗教,它所反映的,仍然是具有强烈汉民族特征的宗教意识。例3中的数句,主要表现中国巫教思想,阴曹地府,阎罗小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巫教思想后来虽然与佛教合而为一,且是通过佛徒讲经来传播,但它的本源仍是贯穿数千年的汉民族原始宗教理念。例4反映的是中国传统婚姻形态的固定模式,门当户对,明媒正娶,下聘礼,择吉日,不仅显示出中国传统道德的严肃性,而且表达出国民通过恪守道德规范祈求幸福的美好愿望。凡此种种,无不带有明显的民族个性,是深深印在国民脑中的固态意识,一代代先民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氛围中日复一日度过的。
作为一个剧作家,把话说到受众的心里,要比卖弄词藻更能引发受众的共鸣,这也是元杂剧极盛于一时而又绵流于后世的重要原因。
元杂剧是中华文化的宝藏,关于元杂剧的语言运用,还可以总结出不少规律性的东西。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上述四方面略作勾勒,但我深感目前学界对元曲语言的研究尚欠深入。假如本文能起到抛砖之功,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元曲语言的研究成果面世,那将会形成一个古白话语法、训诂、修辞乃至元剧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繁荣局面,这样的研究,会远远超越戏剧本身。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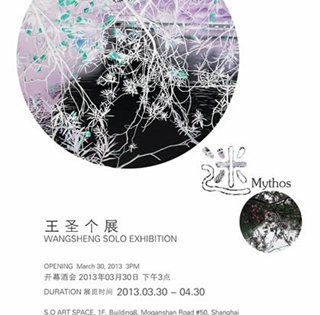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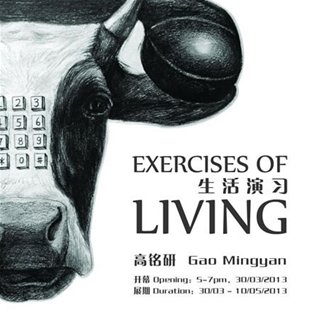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