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元代的大都,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商业兴隆,人物繁阜,市民的娱乐生活丰富多彩。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云:”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耍闹去处”即瓦舍勾栏。高安道《嗓淡行院》也说:”待去歌楼作乐,散闷消愁。倦游柳陌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赏一会妙舞清歌,瞅一会皓齿明眸。趁一会闲茶浪酒。” “棚阑”即勾栏。可见,宋元时期的瓦舍是集市上供人们常年娱乐的民间大型综合性游乐场,而其内设的勾栏演艺与集市贸易密切相关。因此,每天光顾瓦舍勾栏的戏剧观众络绎不绝,难以数计,“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这是汴京的戏剧观众。”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这是临安的戏剧观众。夏庭芝《青楼集志》曰:”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构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这是大都及其他郡邑的戏剧观众。那么,这些戏剧观众主要由哪些成分构成呢?宋元瓦舍勾栏的戏剧观众之一是商人和官吏。
《东京梦华录》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载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载:”都会之下皆物所聚之处,况夫人物繁夥,客贩往来。”同书”坊院”条载:”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载:“临安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同书卷十三”铺席”条载:“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据《马可波罗行记》卷二载:蒙元大都,”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多,计有二万余……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王,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约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妓女多兼演员,她们献艺的主要对象之一便是商人。
以上材料虽然没有直接记载这些商人和官吏入勾栏观剧,但从当时集演艺与贸易为一体的瓦舍遍布汴京、临安和大都来推测,他们必定是瓦舍勾栏的常客。再从《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杂剧的描写也可得到印证,第一折末尼蓝采和对道士钟离权说:”则许官员上户财主看勾栏散闷,我世不曾见个先生看勾栏。”宋元时期,另一批经常光临瓦舍勾栏的戏剧观众是军士。《宋史》卷一百九十四《兵志》载:”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数十万,悉萃于京师。”可知北宋汴京驻扎着大量军队。虽然军中有乐营——钧容直,主要在皇家典礼上演奏音乐,担任仪仗以及表演百戏杂剧,但遇旬休日也上勾栏观看演出。《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云:”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从这则材料推测,”耍闹去处”即瓦舍(游乐场)勾栏(剧场)演出,它必吸引附近休暇的军士。从同书同卷”诸色杂卖”所记更能看出:“或军营放停,乐人动鼓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这里”小儿妇女”当指驻军家属,自然包括“军营放停”之军士。
南宋临安瓦舍专为军士营创,《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载:杭城绍兴闲驻于此,殿前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九也载:故老云: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从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招集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军士及其家属作为南宋瓦舍初创阶段的主要戏剧观众,不在话下。
宋元瓦舍勾栏的戏剧观众除上述几种职业外,其它观众的成分比较复杂。清人潘长吉《宋稗类钞》卷七”怪异”条,记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曾”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黄庭坚写有《鼓笛令》四首,其中第一首下自注”戏咏打揭”(赌博之一种),”后三首词却说的是另一种伎艺,颇似有关散乐的演出”。对其演出时地,我们虽不得而知,但从两宋文人多”以剧喻诗”的风气来推测,他们除观看宫廷演出外,当还常光顾民间瓦舍勾栏观看戏剧演出。宋人郭彖《睽车记》卷五所载”士人便服,日至瓦舍观优。有临坐者,士人与语颇狎”,便是明证。不过他们入勾栏改穿了”便服”,怕招惹非议。张端义《贵耳集》云:”临安中瓦在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这是文人士大夫观众。
《西湖老人繁胜录》载:”遇雪,公子王孙赏雪,多乘马披毡笠,人从油绢衣,毡笠红边。……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消遣。”公子王孙娱乐圈主要在宫廷教坊,但从这则材料来看,他们有时也到民间勾栏看戏消遣。
《梦粱录》卷十九”瓦舍”条谓瓦舍”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游荡,破坏尤甚于汴都也”。这里提到”贵家子弟”观众,他们也常”流连” “游荡”瓦舍勾栏。金元时期也如此。《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演述洛阳府同知之子完颜寿马,因常逛勾栏看戏,迷恋上了杂剧艺人王金榜,被父亲逐出家门,加入王家戏班四处流动卖艺。秦简夫《东堂老劝破家子弟》杂剧就写到一位贵家子弟扬州奴不务正业,整天”不离了舞榭歌台”(第一折——)主要指瓦舍勾栏,以致倾家荡产。李直夫《便宜行事虎头牌》杂剧第二折:“(正末唱)[月儿弯]则俺那生念忤逆的丑生,有人向中都曾见。伴着伙泼男也那泼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里串,几年间再没个信儿传。”元代王结《善俗要义》第三十三”戒游惰”曰:”颇闻人家子弟,多有不遵先业,游荡好闲,或蹴鞠击,或射弹粘雀,或频游歌酒之肆,或常登优戏之楼,放恣日深,家产尽废。”可见当时贵家子弟流连勾栏,以致家产荡尽的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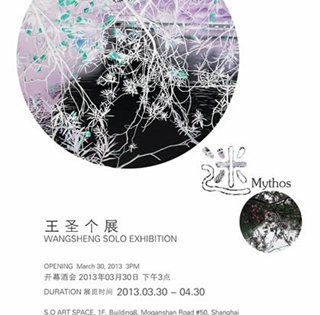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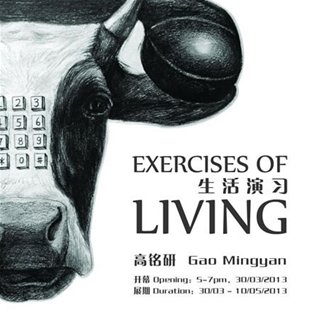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北昆耆宿
北昆耆宿 潮剧的演
潮剧的演 景物造型
景物造型 服饰造型
服饰造型 戏曲文物
戏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