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渔(1611~约1679) 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戏曲理论家。字笠鸿,一字谪凡。号湖上笠翁。原籍兰□(今属浙江),生于雉皋(今江苏如皋)。在明代考取过秀才,入清后未曾应试做官。出身富有之家,园亭罗绮在本邑号称第一。清兵入浙后,家道衰落,遂移居杭州,又迁南京。从事著述,并开芥子园书铺,刻售图书。又组织以姬妾为主要演员的家庭剧团,北抵燕秦,南行浙闽,在达官贵人府邸演出自编自导的戏曲。在此期间,与戏曲家吴伟业、尤侗结交。后因担任主演的乔、王二姬相继病亡,本人亦已年老,境况较前困窘,再度迁居杭州,终老死去。李渔在当时很有声名,但毁誉不一。平生著作有剧本《笠翁十种曲》即《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怜香伴》、《风筝误》、《慎鸾交》、 《巧团圆》、 《凰求凤》、《意中缘》、 《玉搔头》,另有《偷甲记》、 《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醋记》、《补天记》、《双瑞记》等 8种是否出自他的手笔,尚未有定论;小说《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文传》、《肉蒲团》等;杂著《闲情偶寄》和诗文集《笠翁一家言》等。
李渔的戏曲创作数量虽多,但大都为滑稽剧和风情剧,且多情趣低下,甚至流于猥亵之病。就思想内容言,《十种曲》中只有《比目鱼》和《蜃中楼》较为可取。前者写谭楚玉和刘藐姑的爱情故事,刻画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后者把柳毅传书和张羽煮海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歌颂了男女主角为了维护爱情的反抗精神和行为。但自清代以来,通常认为《风筝误》是李渔的代表作,此剧写韩世勋与詹淑娟婚姻故事,情节曲折,误会丛生。论者认为它关目布置很工,宾白言谈得当,曲词本色平易,但也批评它有堕入恶趣的严重缺点。
李渔的小说虽大都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但亦多格调低下,思想陈腐之病。所写内容以男女婚姻为主,情节比较曲折。
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却取得杰出成就。《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录出单印,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词曲部》论戏曲创作,含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项;《演习部》论戏曲表演。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他充分认识到戏剧结构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性,声称"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并就结构问题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具体方法。他强调宾白的个性化,即所谓"语求肖似","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又提出戏曲之格局要求"小收煞"处,须"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最后的"大收煞"既要使重要角色"大团圆",又要注意"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诸如此类,都堪称卓见。李渔的戏曲理论亦有糟粕,如强调维系封建教化、"务存忠厚之心"、点缀"太平"景象等等。但就对编剧技巧的探索而言,则在继承王骥德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经验,把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渔的戏曲理论
李渔的曲论,在我国戏曲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意义,很值得研究。李渔(1611—1680)年轻时曾热衷科举,入清后才投身文坛,著作有数十种,以传奇集《笠翁十种曲》和杂著《闲情偶寄》为最著名。李渔的文艺生涯与当时一般文人很不相同。在金陵开设芥子园书坊是为了赚钱,领着家庭戏班奔忙于达官权贵门下是为了赚钱,甚至赋诗作文编撰剧本也无不是为了赚钱。因而正统封建文人“以俳优目之”(《曲海总目提要》),卑视他的人品。可是文坛名流如王士禛、周亮工、尤侗、吴伟业、杜于皇、于澹心等,却欣赏他的文艺才能,乐意和他往还。事实上,李渔是一个依附封建士大夫的专业戏曲家、理论家。他为戏曲创作和理论探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李渔的曲论主要见于《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另有“声容部”虽内容驳杂,也偶涉曲论)。现在习见的《李笠翁曲话》,是后人将这两部分单独刊印而成的。
李渔特别重视戏曲结构,认为自《中原音韵》一类韵书曲谱问世之后,音律已不再是曲论着重探讨的问题。“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见《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以下不注出处者,同此书),结构先于音律,是戏曲创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理应引起理论家的足够重视。“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李渔突破习惯看法,把结构问题提到了“首重”的位置。他用“造物赋形”和“工师建宅”作比喻,来阐明结构的极端重要。“工师之建宅……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戏曲创作也是如此,剧作家“不宜卒急拈毫”,匆忙动笔,“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只有结构成熟,方可奋笔疾书。结构是否妥善完整,关系到剧作的成败优劣,不能等闲视之。可是当时不少剧作者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澹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局规模之未善也。”研究戏曲结构,元明曲论家已经开始。但大都局限于论述套数曲,即剧曲的布局、章法等等。李渔则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把注意力集中到“结构全部规模”,开始研究戏曲的矛盾冲突。这对于戏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结构第一”之下,列有“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等专节,开拓了研究戏曲结构的新领域。
“立主脑”是李渔结构论的主干。什么是“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又说,剧本中为主的“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琵琶记》中蔡伯喈“重婚牛府”,《西厢记》中张君瑞“白马解围”,就是它们的主脑。可见“主脑”,就是体现作者“立言之本意”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只有“立主脑”,才能突出主要矛盾,更好地表现作者“立言之本意”。李渔以为没有“主脑”的剧本,充其量不过是断线之珠,无梁之屋,有见识的艺人必然望而却步。“立主脑”,离不开“减头绪”和“密针线”。一个剧本如果头绪纷繁,“旁见侧生之情”众多,其戏剧冲突必然枝蔓不清,“主脑”不立。头绪既清,紧接着还要“针线”紧密。关于“密针线”,李渔有一个妙喻,“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这些见解相当精辟地揭示了编剧构思的特殊规律。
《闲情偶寄·词曲部》的“审虚实”、“戒荒唐”等小节,论及“虚”、“实”及其相互关系。众所周知,剧本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细节描写,都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同时,任何成功的作品又都不是生活的照搬,容许必要的艺术虚构。所以历来剧作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生活真实和艺术虚构在作品中辩证地统一起来。对此,李渔用“姓名事实,必须有本”和“传奇无实,大半寓言”相结合的办法予以解决。当然“有本”不等于照搬照抄,更不是落入前人窠臼,拾他人牙慧。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剪裁,达到“既出寻常视听之外,又在人情物理之中”(《香草亭传奇序》),“凡阅传奇而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这种见解和某些排斥艺术虚构,将戏曲作品视同历史记载的认识比较起来,更符合戏曲的艺术特点。
李渔反对把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恶劣倾向,认为拼凑出来的不是“新剧”,而是“老僧碎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缺少艺术感染力。“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只有创新,戏曲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他指出,戏曲和诗文一样“随时更变”,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变革,决不停滞不前,凝固不变。“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深刻地揭示了“新”和“变”的内在联系,创新存在于变更之中。因此,传统剧目也不能简单照搬,上演时也要“随时更变”,变旧为新,有所变更。因为“世道迁移,人心非旧……,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以拂听者之耳。”我国古代的进步戏曲家,总是对传统剧目进行不断的加工和修改,使之变旧为新。他们的努力,推动了戏曲现实主义代代相传,不断发展,而戏曲正是在变旧为新中得到发展提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渔的“随时更变”、“变旧为新”,和戏曲“推陈出新”的客观规律相当接近,值得重视。
论述戏曲语言的特点,《闲情偶寄》有“词采”、“音律”和“宾白”等节。李渔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只重视曲词,“视宾白为末着”的习惯看法。指出戏曲之于宾白,好比“栋梁之于榱桷”,“肢体之于血脉”,非但不可缺少,而且“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彼,竟作无用观者”。“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剧作家要把宾白“当文章做,字字俱费推敲”,不能掉以轻心,以为“随口出之即是”。李渔以为重视宾白,提高宾白的地位,是他的贡献,“传奇中宾白之繁,实自予始”。
我国的传统戏曲,由于受表演艺术分行的制约,因此人物性格的刻划与角色“行当”的区分很有关系。对此,李渔在“戒浮泛”节指出,设计人物语言,“但宜从脚色起见”,如花面不妨粗俗,生旦则宜隽雅舂容,一定要注意脚色区分的特点,不能彼此混淆,破坏了人物形象的统一。关于戏曲语言的个性化问题,李渔说:“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要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个性特征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如此明确地阐明语言的个性化,这在古代曲论中确实并不多见。
李渔主张戏曲语言应努力做到雅俗共赏,既通俗浅显,又富有艺术魅力。“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根据戏曲语言受舞台演出和观众文化程度限制的特点,要求剧作家力求通俗浅显,明白易懂,切忌晦涩艰深。“凡读传奇而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通俗浅显并不是不讲究艺术美,而是“于浅处见才”,“意深词浅”,耐得咀嚼。
关于戏曲的批评鉴赏,李渔以为,首先鉴赏者要真正懂得戏曲的艺术特点。因为从创作者方面说,“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编撰剧本,目的在于舞台演出,只有“观听咸宜”,“几案氍毹,并堪赏心”的,才算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所以鉴赏者也不能用赏鉴一般文学作品的眼光看待剧本,“上下千古之题品文艺者,看到传奇一种,当移心换眼,别置典刑”。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李渔批评金人瑞的《西厢记》评点,文字上穷幽析微,令人折服,却未能把“优人搬弄之三昧”,即舞台演出之精髓揭示出来,算不得好剧评。其次,强调鉴赏批评中“情”的作用:“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如其离合悲欢,皆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发冲冠,能使人惊魂欲绝”。进一步指出作品是通过“人情”去打动鉴赏者的感情。作品只有在“合人情”,“为人情所必至”的情况下,才能引起鉴赏者感情的激荡回旋。简言之,戏曲鉴赏离不开共同的“人情”。这实际上已涉及艺术鉴赏中的共鸣问题。第三,提出了“情”、“文”、“风教”“三美俱擅”的批评准则。同时又说,一个剧本即使“情事新奇”,“文词警拔”,却“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仍然不是好作品(均见《香草亭传奇序》)。“三美”之中又强调了“有裨风教”。毋庸讳言,李渔说的“风教”,无非是“忠孝节义”以及替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一类糟粕。可是,所谓不能“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云云,显然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效果。可见,所谓“三美俱擅”,其实是首先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社会效果。这对于后人开展戏曲批评,确立批评准则,并不是毫无参考意义的。
最后,《闲情偶寄》在戏曲理论组织体制上的贡献也值得一提。历来的曲论专著,多半是随笔式的,侧重论述记载诸如音律、表演、剧目、本事等某一方面。晚明王骥德的《曲律》第一次把戏曲理论分成四十个专题,开创了综合论述的新体制。但《曲律》仍有旧体制的痕迹,《闲情偶寄》又有发展。它只述理论问题,不记曲谱格律,确定了研究范围。在词曲、演习两“部”之下各设若干“章”,各“章”有总论性的序言;章之下分若干“节”,各节有醒目的标题。这种“部、章、节”的区别划分,反映了李渔在理论的系统性、明确性上比他的前人有了一个飞跃。在二“部”,十一“章”,五十三小“节”中,囊括了戏曲理论的主要问题,把它们组织得有纲有目,层次清楚,轻重分明,开了古典曲论组织体制的新生面。
李渔戏曲理论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当时正是传奇创作空前繁荣的巅峰之后,剧本创作和舞台表演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总结这些经验,借以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已是时代向理论提出的迫切任务。同时,明代中叶以后,徐渭、魏良辅、李卓吾、沈璟、汤显祖、王骥德、吕天成、祁彪佳、凌濛初等的理论活动,以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把我国的戏曲理论批评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李渔正是在这样优裕的历史条件下,以他卓越的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虽然李渔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他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观,著作中夹杂了大量的封建糟粕。然而,他总结的前人创作和演出的丰富经验,以及关于戏曲艺术的许多真知灼见,无论对于后来的创作,还是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戏曲理论批评宝贵的资料。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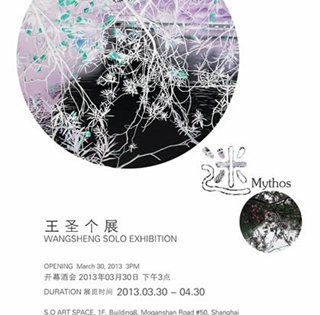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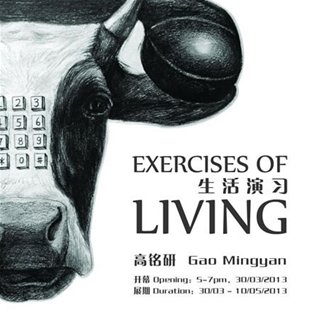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传世美谈
传世美谈  历尽沧桑
历尽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