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稍知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汤显祖的名字。但是,在明代中叶的戏曲界,汤显祖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另一个名字——沈璟响亮。在现存的明中叶后的戏曲论著中,处处可见沈璟的名字,他的作品被冠以赞誉之辞,他的理论见解经常被引用,有的盛赞他于明传奇“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有的则称他为“曲坛盟主”,他和他的作品总是排列在汤显祖之右。这一切表明,他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少年进士到弃官归里
嘉靖三十二年(1553),沈璟出生在距苏州城不远的吴江县城。吴江县城又叫松陵镇,这里紧靠美丽的太湖;运河从城外流过,小河交叉穿错,处处呈现着水乡的秀丽景色。沈璟之父沈侃在科场上蹭蹬多年,却与功名无缘,儿子自然是他的希望。也许正是为了给他争气,沈璟读书很是上进,21岁就参加了应天乡试,考中了第17名举人;22岁参加会试,为第三名,廷试二甲五名,顺利地成了少年进士。
沈璟先后在兵部、礼部、吏部任职,官职也由主事升为员外郎,但是,34岁时,他的仕途却碰到了一次挫折: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也不给生下皇子的王恭妃封号。一些朝臣生怕皇帝做出有悖礼制的事来。纷纷进谏、要求册立太子并给王恭妃封号,沈璟也给皇帝上了一疏,因而触怒了皇帝,遭到降职二级的处分,并被令离开京城回家乡办公事。
这次挫折时间不长,过了一年他重被起用,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次年又升为光禄寺丞。但就在这时,另外一件事发生了:他在顺天乡试中录取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的女婿李鸿。本来,这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李鸿是个有才干的青年,后来还成了一个有名的与矿监税使作斗争的正直官员;沈璟为人正直,爱惜人才,录取李鸿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才干,并非讨好申时行。然而当时,申时行所代表的内阁与朝中的一批言官矛盾较深,申时行的女婿李鸿被录取成了言官们攻击内阁的一个把柄,沈璟也被卷入了这种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更为了逃避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他决定激流勇退,辞去了官职,回到了家乡吴江县,这年他才37岁。
从袖手风云到戏曲癖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璟对政治已经冷漠,回到家乡以后,他决意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
居于乡里,他开始对家乡的戏曲活动感兴趣。苏州素称歌舞之乡,吴江县也是如此,这里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有家庭演出,有民间演出,前者如顾大典家,“家有清商一部”,“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潘柽章《松陵文献》卷九);民间演出更多,或者是职业班社商业性演剧,或者是迎神赛会及节日期间的戏剧活动,苏州城内更是日日演剧,夜夜笙歌。在这个“歌舞之乡”的艺术熏陶下,沈璟迈上了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
沈璟开始仅与蓄有家乐的顾大典共同从事戏曲活动,后者也是一个退职官员,二人境遇相同,他们“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风流,多蓄声妓盖自二公始也”(同上)。李鸿在为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作序中说:沈璟“性虽不食酒乎,然间从高阳之侣,出入酒社之间,闻有善讴,众所属和,未尝不倾耳注听也。”不仅于此,他还躬身登场,据他的学生和朋友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他“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时招僧妓饮酒”;他的朋友王骥德在《曲律》中说他“生平故有词癖,谈及声律,辄尾尾剖析,终日不置”。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沈璟对戏曲的迷恋。可见,沈璟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并非偶然。
“场上之曲”的提倡者和实践者
四十年来的古典文学和戏曲史研究中,“汤、沈之争”是一个热点。的确,汤显祖和沈璟在艺术观点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我们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艺术观点呢?恐怕还应该将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辩证的分析。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了“情”“理”之分以及“情必胜理”的主张,而沈璟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事实上,两者的创作的侧重点也确实不同,汤显祖不仅创作戏曲,也创作诗文,还写了不少与友人们讨论社会、人生、思想的信札,而沈璟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戏曲方面。单以戏曲论,沈璟在数量上远过汤显祖,他创作了“属玉堂传奇”十六种,是有明一代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他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遵制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著作,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作品。简单地说,沈璟对戏曲艺术的贡献在于大力提倡“场上之曲”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之。
元代前期,大批剧作家生活于市井之中,他们熟悉瓦舍勾栏中的戏曲演出舞台规律,因而他们创作的杂剧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符合舞台规律,是当行的“场上之曲”。但是明代前期,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获取高官厚禄,戏曲作家数量急剧下降,染指戏曲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远离戏曲舞台实践,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成了“案头之作”,它们文辞骈丽典雅,缺乏戏剧性,难以演诸场上。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沈璟率先出来倡导“场上之曲”,他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有利于戏曲走出“案头”演诸场上的理论。
沈璟的戏曲理论包括格律论和本色论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两方面内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首先,格律论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入手,要求戏曲能演诸场上。中国戏曲有其独特的规律,曲的写作就是其重要规律之一。戏曲不同于西洋歌剧,后者是戏剧作家创作出歌词再由音乐家谱曲,而戏曲则没有音乐家谱曲这一环节,它是靠一定曲牌将作家与演员联系起来,剧作家按一定曲牌的规则写作曲词,演员则按一定曲牌的规则演唱,曲牌是作家写作与演员演唱之间的桥梁。因此,剧作家必须熟悉曲牌,严格按照曲牌格律的具体规定写作,才能让演员唱起来顺口,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元杂剧音乐由诸宫调发展而来,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宫调曲牌体系,因而作家和演员们能够很好地配合起来。但是明传奇由南戏发展而来,南戏的音乐来源是民间村坊小曲,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宫调曲牌体系;明代前期的传奇作者又都远离舞台实践,对曲牌写作的格律不了解,由此而导致了作品与舞台演唱的脱节;另外,昆山腔虽然受到欢迎,但如何为这种新腔归纳总结出曲牌格律,以便更多的剧作家创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沈璟精心研究曲牌格律,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对南戏传奇以及昆腔曲牌格律进行归纳、总结,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范例;他又编撰了《唱曲当知》、《论词六则》、《遵制正吴编》等曲学著作对作家创作及演员演唱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辨析。总之,要求“词人当行,歌客守腔”(沈璟〔二郎神〕套曲,见天启刻本《博笑记》)就是沈璟格律论的精髓所在。其次,本色论不仅要求戏曲演诸场上,而且还要令观众能解能懂。沈璟并没有片面强调戏曲唱的方面,而是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易懂,他甚至批评自己的《红蕖记》过于骈丽;他推崇宋元南戏的语言,正因为它是从民间产生的,带有较浓的民间生活气息,通俗浅近,质朴古拙。因此,本色论从反面证明了格律论正是要求戏曲能够演诸场上,而本色论自身又具有反对“案头之作”语言骈丽典雅的积极意义,其指向仍是要求戏曲必须是“场上之曲”。
沈璟不仅提倡“场上之曲”,在创作实践中还努力实践这一主张。他的现存作品确实都符合曲牌格律、语言通俗,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可演性;此外他在创作中还试图从更多的方面使作品成为“场上之曲”,如,他开始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力图使作品带有更多的戏剧性;他开始注意缩短传奇的结构体制,《博笑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一共才有二十八出,本身的结构在明传奇中就属超短的,而且沈璟还尝试着在这二十八出中表现十一个小故事,它们合在一起是一本传奇,但拆开来又可以单独演出,这一尝试实开晚明折子戏先河。
不仅仅是“吴江派”的首领
1949年以后的不少论著都认为明中叶有两到三个戏曲创作流派,而“吴江派”都在其中,沈璟正是“吴江派”的代表或首领人物。我们可以结合明中叶戏曲发展的具体实际,来看沈璟在其中的贡献和地位。
作为“场上之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沈璟实际上所触及的问题正是明传奇发展中急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明传奇如果不从“案头”走向“场上”,就必然死亡。因而这也是大部分传奇作家所瞩目和担忧的问题。沈璟大加提倡“场上之曲”,不仅从理论上进行研讨,而且在创作中积极实践,就赢得了一大批响应者,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明传奇创作的“案头之曲”的倾向被扭转过来,从而形成了明中叶后传奇创作、演出大繁荣的新局面。所以王骥德十分称赞沈璟,说他对明传奇的“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曲律》)。正因为此,推崇追随他的是明中叶曲坛上绝大多数作家,而并非今天划归“吴江派”的寥寥几人。王骥德、吕天成、卜世臣、冯梦龙等不说,其它如毛以燧、沈宠绥,同样推崇沈璟;凌蒙初虽对沈璟的创作有微言,却未否定他的理论贡献;从未被划为“吴江派”成员的徐复祚也赞颂沈璟的格律论,认为是“皎然指南车也,我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曲论》)同时他又继承了沈璟的本色论,主张“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畯红女闻之而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同上)即使与沈璟艺术观点对立的汤显祖也在现实面前与沈璟有部分的一致,他是因为沈璟改编他的《牡丹亭》为《同梦记》而对沈璟不满,但并未彻底否定沈璟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中,他也感到对曲牌格律的不熟悉是一种缺陷。值得指出的是:沈璟虽然对明中叶曲坛的大多数戏曲家有影响,但是他自身的理论也不完备,而且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而这些不足和缺点又是由他的追随者们予以批评并补充完善起来的,他们和沈璟一同完成了明传奇由“案头”到“场上”的理论准备和倡导,从而促进了明传奇繁盛局面的到来。沈璟不仅仅是“吴江派”首领,而且不愧为明代曲坛的一代“盟主”。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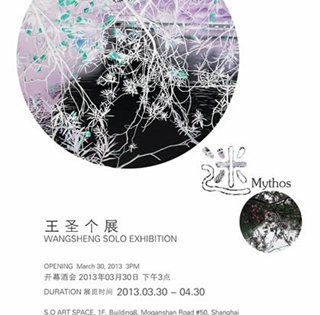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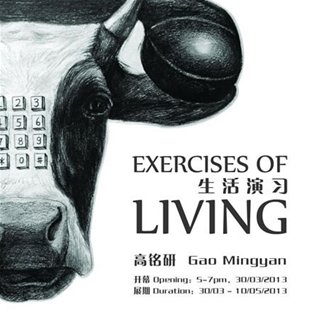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传世美谈
传世美谈  历尽沧桑
历尽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