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彬
6000多部中国文学史,100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昨日(16日)又为这个庞大的数字“加了1”。但与其他绝大多数只是为了出版而出版的“文学史”系列图书不同的是,昨日在上海首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必将引起中国学界关注,因为他的作者是那个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顾彬。在昨日的首发式上,顾彬说,他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而与会的作家学者也“失望”地发现,这部文学史中没有类似“垃圾说”这样的猛料,“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作家孙甘露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刚刚出版,顾彬还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中国戏剧史》,“所以我的记忆都停留在清代和京剧上”。
“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编著完成。谈到编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回忆说:“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他认为中国以前发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文章都不是很专业,“都是在对历史进行介绍,譬如这人在何时写了什么文章等,没有对其人生或是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但顾彬的雄心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些中国学者建议我应该多研究一些哲学或神学。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在德国甚至欧洲都不会有人会去写中国文学史,不是他们不懂,是我觉得他们都懒得动笔。也有人准备与我合作,可是过了几年后,书没出来,这些人也都没联系了。”
在这本文学史里,“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面世,“在欧洲卖120欧元,中国只要58元人民币,太便宜了!”顾彬开玩笑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评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几百年后,我们只会记得这些文本,而不会再记起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本来以为书中会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但现在可能要让我们失望了。——陈思和
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孙甘露
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文学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镜像投射,比如鲁迅给多少字,茅盾给多少字都会有所限定。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张闳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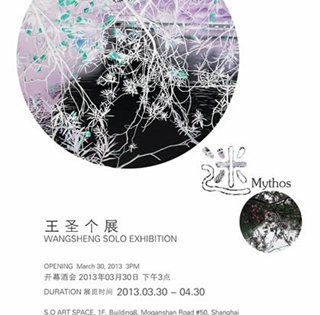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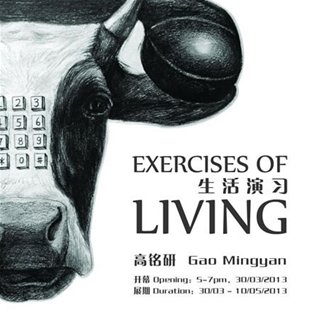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杰出诗人
杰出诗人 知名女作
知名女作 图书市场
图书市场 秘鲁作家
秘鲁作家 芬兰出版
芬兰出版 《红楼梦
《红楼梦 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 惹了祸的
惹了祸的 徐德亮出
徐德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