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5月下旬,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第一次访华。十天中,他游历了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个城市。9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回忆道:“地震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间。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
5月28日22点,阵雨之后的绍兴,空气新鲜。帕慕克绕着绍兴酒店走了大半圈。此时,没有演讲、采访、签名。帕慕克放慢了脚步,轻柔地踩着地,看起来,没什么力道。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说,从帕慕克抵华以来,这种清静很难得。
7天前,帕慕克和女友、2006年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抵达北京。这是帕慕克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
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帕慕克在北京、绍兴、上海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自帕慕克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出版其中文版小说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想方设法欲邀请他来华。2007年3月、8月,坊间数次传出帕慕克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但因为帕慕克受到土耳其国内极端民族分子的死亡威胁,流亡国外,导致计划全部泡汤。今年3月,一场以帕慕克为头号暗杀对象的密谋被破获,参与密谋行刺有13人,其中3人被警方逮捕,现已开庭审理。帕慕克说,为了保护他,他家直到现在还有警察站岗,“在土耳其等一些高压政策的国家里,敢说真话的作家肯定会受到生命威胁。但作为普通人,我希望有生活的权利,我不怕,我只想写作,写出自己的想法。”
如今,帕慕克一年有四个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课。他说教书权当旅游,日子先这样凑合着过。
刚到中国,在表达完对四川地震灾区的同情后,帕慕克就急不可待地说:“在北京这几天,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参观博物馆,特别想看中国的传统绘画,我是中国绘画的fans。相对西方绘画来说,中国绘画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5月26日晚,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帕慕克的私人宴请上,有学者对他说,你了解细密画,但不了解中国绘画。帕慕克回答,此次中国行,就是来补课的。他几次对铁凝说,会把中国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里。
“我喜欢旅行,旅行总能给我各种各样的想法”,正如以往每次为写作去各地搜集素材一样,帕慕克的中国行也是有备而来。
缺席自己作品的研讨会
到中国下了飞机,帕慕克对他的中国之行的陪同许金龙说:“我就是一个大孩子。”
5月24日中午,帕慕克在北大附中四楼学生食堂里吃饭。饭前,帕慕克和食堂大厨学包饺子。
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次为帕慕克设宴,一次在宫廷菜馆仿膳,一次在茉莉餐厅。帕慕克好奇于老北京点心“驴打滚”如何滚起来。见到好吃的点心,他动手就拿。
姚映然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责任编辑。以前读帕慕克的作品,姚映然觉得他是一个羞涩的人。但见面后的感觉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写作精准,思辨逻辑力强,很有控制力,但对日常生活特别感性,一发现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像小孩一样。如果反感,就会一下子消沉,转身就走。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帕慕克满头花白头发,笑起来,一脸狡黠。他平时不喜欢应酬,也不爱出席派对,甚至没什么朋友。以正常成年人的标准看,他不世故不圆滑,开心与否全在脸上。有朋友说帕慕克“奇妙地结合了文学天才的智慧、孩子气的天真幼稚”。
5月23日,为期一天的帕慕克作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举行。当年大江健三郎访华时,其作品研讨会也在这里举行。
帕慕克和大江是朋友。但是,帕慕克在研讨会上的表现和大江健三郎完全不同。研讨会开始前,帕慕克就自己的写作经验做了20分钟发言。讲话结束前,他出人意料地说:“对我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的作品里也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可以让大家进行不同的解读。每当我听到不同的解读时,我都觉得这些解读者在阅读我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我想隐藏起来的。所以当面听大家的解读,对我来说,有点困难。”说完,帕慕克便离席而去。与会专家学者面面相觑。研讨会在帕慕克的缺席中进行,下午3点就提前结束。
有学者指责帕慕克“无礼”、“随便”。人们拿他和当年的大江健三郎相比,“大江毕竟是苦孩子出身,随和”。
也有学者为帕慕克辩解。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说:“帕慕克本来就不想参加研讨会,我们尊重他的决定。钱钟书也不喜欢参加研讨,吃鸡蛋没必要认识下鸡蛋的母鸡。”副研究员侯玮红猜测,帕慕克的离席是“因为害羞”。
在世界范围,帕慕克几乎不出席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在去年6月由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首届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两天的会议中安排了半天讨论帕慕克的作品。帕慕克也没有出席。
在北京,帕慕克客气地说,“出席研讨会,我虽然不觉得尴尬,但觉得怪怪的。如果35年前,有人告诉我,在中国举办一个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我会觉得那是做梦。我并不想因为自己而打破这个神话。事实上,大家今天如果没有发现我在场,可能会更好。”
从研讨会上出来后,帕慕克带着德赛逛北京,并且谢绝了外文所在崇文门烤鸭店的宴请。为了尽情游览,他不吃中饭,还对催促他的工作人员抱怨。
帕慕克游览颐和园时,不巧,排云殿不对外开放。此地是慈禧举办60岁大寿之处。帕慕克于心不甘,隔着窗户,一边说“我恨你”,一边沿长廊绕大殿,从窗户外往里看。“他那个爱啊,看了很久不肯走,”许金龙说,“眼看在新浪网直播专访的时间就要到了,只好拉他走。他非常不愿意,嘟着嘴。到了新浪楼下,他说,需要一杯咖啡把脸色转过来,不能用这个脸色去面对中国网民。”

帕慕克喜欢拍照,走到哪里拍到哪里。
书呆子作家逛北京
25日晚,帕慕克和女友德赛在一间淡黄色小楼的露天阳台上,吹着晚风,看不远处的阳台上北京人进进出出。这是一个英国女人改造的北京有名的微型图书馆“Book Worm”(书虫)。露台上,帕慕克又举起了他那个蓝黑色的数码相机。他喜欢自拍,走到哪里拍到哪里,而且技术很好,常常拿给德赛炫耀。
帕慕克听姚映然说,在琉璃厂可以买到画作,就要求去琉璃厂。他在琉璃厂买了一大堆书。帕慕克和德赛都是爱书之人。德赛在西单买了英语版的鲁迅作品,鲁迅是帕慕克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1960年代后期,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出版。帕慕克十几岁时,就读过《呐喊》。帕慕克说,在土耳其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所以他一生都在买书。“我是一个买书人,还是一个复印书的人,这有点可笑。我在家里有16000册书。”
22日,帕慕克欣赏了故宫中部分不对外展览的藏品。在专家的讲解下,帕慕克了解了南北派画法,他看得很慢。25日,游览雍和宫和孔庙时,他为了多看,宁可不吃中饭,下午饿着肚子签售图片。除了社科院安排的八达岭长城等游览项目外,帕慕克还提出要看看恭王府。他坐在人力三轮车上,穿梭于后海熙攘的游客中。
帕慕克对北京如此的着迷,也许是他又在为写作“做调查”。
每次写作前,帕慕克都会做大量调查。他说作家分为两种,一种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另一种会做些调查研究。“我当然是第二类作家,很明显,我是一个有点书呆子气的作家,愿意为了写作进行哲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比如阅读、拍照、摄像等。虽然90%的考察结果,并不会用在小说中,但是我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调查让我熟悉创作主题,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
2000年,帕慕克开始为第7本小说《雪》准备。小说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为了真实地描写“卡”的生活,帕慕克去了法兰克福。在书里,每天清晨,“卡”从家出发,去市立图书馆,图书馆是卡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现实中,帕慕克和当地导游一起体验这段路程,他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大街,经过性用品商店、土耳其杂货店、肉店以及一些土耳其烤肉店。他们还去了“卡”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多冗长、看起来不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我会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会问自己: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是这样开过街道吗?”
对“卡”的另一个活动地点“卡尔斯”——土耳其东北部小城,帕慕克也作了同样的调查。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商店地摸索卡尔斯;他和失业者聊天——他们终日在咖啡馆度过,而且没有任何找到另一份工作的希望;他和大学预科生聊天,和穿便衣警察聊天,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警察都跟着他;他和报纸的出版发行人聊天——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250份。
后来,这些素材写进了《雪》。那些警察和帕慕克也成了朋友。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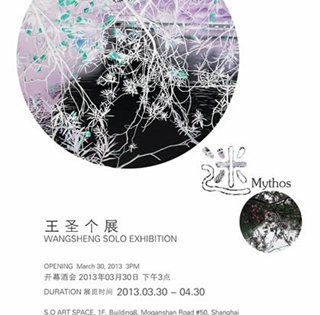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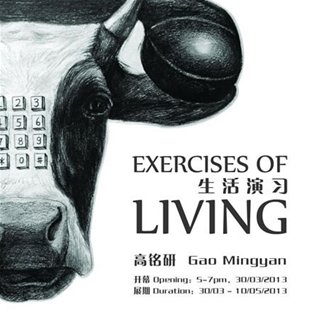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杰出诗人
杰出诗人 知名女作
知名女作 图书市场
图书市场 秘鲁作家
秘鲁作家 芬兰出版
芬兰出版 《红楼梦
《红楼梦 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 惹了祸的
惹了祸的 徐德亮出
徐德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