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法比安·维特的《事故共和国》(上海三联,2008年6月)讨论了安全生产的法律建构问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法律建设的推动作用毋庸赘言。《事故共和国》的副标题是“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揭示了隐藏在工伤与赔偿制度背后的政治与法律博弈。有美国学者认为该书“谈到了手指是值30还是60美元,触及了苦痛的政治表述,亦即苦痛如何被衡量、被商品化、被表达、被压制……”这些痛苦的经验曾经转化为美国法律建设的动力,导致在1910年就建立了工人赔偿体制,并且塑造着美国的社会政策。
由近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后人顾拜旦男爵编撰的《“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生》(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以丰富的图像资料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对于曾置身于奥运热潮中心的国人来说,这位“奥运之父”的许多人生与思想特征仍是很陌生、或者是不愿意了解的,比如他的贵族出身、神学指引、古典学向往、教育学关怀;还有他的古希腊梦和近代英国梦的浪漫主义向往等等。顾拜旦把奥林匹克主义定义为一种人生哲学不是一种空泛的说法。古典学在我们今天这种被实用功利主义彻底宰割的教育体系中简直近乎天方夜谭,但我可以说,中国人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现代文明就有多远;狂热地涌向街头的人群离古典学有多远,离真正的奥林匹克源泉就有多远。
英国学者马克·吉罗德《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的主题是关于城市与人的生存问题,其视界、旨趣非常恢宏、深远,它以众多城市的个案分析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是如何塑造着城市的发展面貌。
彼得·伯格的《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开篇就指出,社会学家并非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些社会工作者、调查者、改良者等等,然后在全书中层层深入地坦陈什么是理想的社会学家:一个充满人文主义情思的人,在社会中是一个智慧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警惕的怀疑者、敏锐的发现者、甚至是自由的游离者。伯格此书被誉为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但又全无冠冕堂皇的学究气,而是如书名所讲的是一次“邀请”(invita-tion),欣然赴会者自然可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书中有些叙述并非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理,但其所思正中我曾经之想,如面对城市中万家灯火,想到如何洞悉社会表象下的真相,这就是社会学的视角:揭示支配社会结构的权力机制。社会学的反思视角使他在“不能改变或破坏社会”的时候,循着“退让”、“策略”、“角色距离”等路径进入到“一个有用的概念———游离(ecstasy)”。它是指适时的置身局外、适时地步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与自己日常扮演的角色拉开一段距离。
近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食品安全风暴使人们极为关注食品生产的真相,但是人们应该知道比技术的真相更重要的是经济学上的真相,因为这才是假、毒之源;另外,在风暴中人们会更加迫切地责成公共管理机器的庇护,也就是大兴问责之风。然而,加拿大法学教授乔尔·巴肯的《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却很清晰、很简捷地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一方面国家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免受公司所害的力量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国家维护公司利益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我们不应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管制公司,而应该思考国家与公司的利益是如何连结在一起的、国家会为了谁的利益来管制公司。这可是一个事关“存在,还是毁灭?”的真问题,远非单纯的向官员问责所能解决。
纳扬·昌达《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中信出版社,2008年5月)力图阐明的是,早在1961年“全球化”这个术语在英文字典中出现之前,人类的生活早已是经由各种方式“绑在一起”,似乎是印证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古老格言,而且可以追加一句:太阳底下只有新术语。作者绝非是“全球化”的盲目鼓吹者。在最后一章“前路”中,作者对人类文明经过“全球化”洗礼后的富庶与贫困、民主与独裁、挑战与危机等作了全面的总结,“我们清楚地知道,人性中的种种希求、渴望与恐惧已将我们的命运编织在一起,既无法拆解,也不可能复原。”这就是“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而今日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已经使我们痛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内涵。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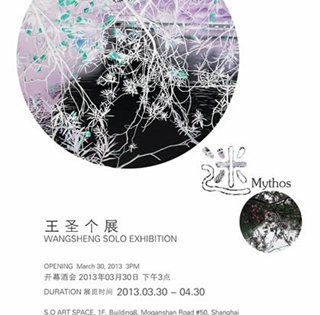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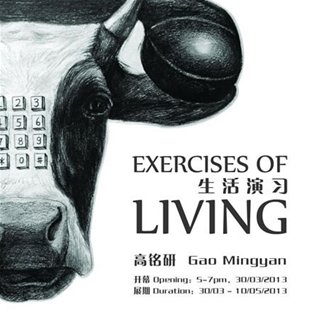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杰出诗人
杰出诗人 知名女作
知名女作 图书市场
图书市场 秘鲁作家
秘鲁作家 芬兰出版
芬兰出版 《红楼梦
《红楼梦 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 惹了祸的
惹了祸的 徐德亮出
徐德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