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演了一个多月又出事体哉。福安场子小,后台只能容纳几个人,衣箱放不下,放在后门口的过道里。演员换衣、化装都不方便。华传浩又嚷开了:“场子介瘪脚,螺丝壳里做道场,介许多人挤在一起,连动物园都不如。”周传瑛听了回敬几句:“奈有本事,自已去寻好地方。能够到螺丝壳里做道场巳经勿错哉。”就这样两人吵了起来,王传淞对华不满,帮周与华吵,那天我妻子带领三个小囡从苏州到上海,俚笃乘船来,在苏州河大统路码头上岸,我去码头接人,勿在游乐场里。自那次吵架后,周传瑛与王传淞决意要离开戏班,认为长此下去经常吵架也不是办法,大家分开一段时间会好一点,劝也劝不住。俚笃两人在1941年前后离开戏班,到国风苏剧团,与这件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 
无奈散了伙
没过多久,八,一三事件暴发,日本人轰炸上海。福安游乐场地处小东门,属旧城区地界,过去伲称中国人地界。开始日本人还不敢轰炸租界,因为那时日本还未与英美开战,炸弹掼在中国人地界中。小东门、十六铺一带,因靠黄浦江码头,市面特别好,商人、小贩都到这里来做生意,成为日本人攻击的目标。伲的家大多数在租界里,一听说日本人要掼炸弹,就逃回租界。一天福安游乐场的人来找我,说游乐场被日本人炸掉了,“仙霓社”管服装的曾长生也来说:“放在福安游乐场的衣箱也全部炸毁了,一件也不存。”天哪,伲吃饭家什呒没了,今后怎么办?几个师兄弟赶到小东门,只见一片狼藉,福安游乐场成为瓦砾废墟,看到这个场面,伲都惊呆了。戏班的命那能介苦,十几年前,伲刚从传习所学艺出山,去杭州第一舞台公演,在去杭州的火车上,不知什么地方来的枪声,一粒子弹打死领班浦仁来,(穆藕初公司里的职员),伲当时人小,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枪声中伲踏上社会,现在伲正在苦难中挣扎,一颗炮弹炸毁行头,在炮声中结束戏班生涯,历史是那样的无情。
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我伲戏班不发生矛盾,在大新公司游乐场继续演下去,就不会发生行头被作的事情,因为大新公司地处南京路,属公共租界范围,抗战初期,日本战火还没有影响到租界地区。伲戏班中管服装的曾长生,是施桂林的小舅子,也唱过戏,工旦,因年纪大演不动戏,就管管服装。但此人做事此较马虎,伲在福安演出时,因为战争关系,观众越来越少。听人说,日本人要进攻南市,南市保勿牢,我叫曾长生清点行头,要做两本帐,俚说不会做。点行头前,我还请俚吃饭,自己掏腰包,因为我是当时戏班负责人。做头头总是要吃亏的,赔的钱小意思,有时吃力不讨好,不能被人理解。第二天点行头,缺少一件水衣,被徐传溱拿去了,当时他将水衣穿在里面,到典当店当五元钱,买鸦片吃,俚吃鸦片上瘾头,什么都不管。我叫俚将当票取出来,由我出钱去赎回来,贴了五元钱。行头被炸,箱子里的东西是否被人拿过,这是一个迷,因为曾长生管理不严,大家存有这样的疑问。
没有了行头,“仙霓社”实际上己经不存在,大家只好散伙,各奔前程。就在戏班解散不久,发生了两件令人揪心的事,即赵金虎和赵传君的猝死。赵金虎自“仙霓社”散班后,他到滑稽戏班吹笛,后来伲十二个传字辈师兄弟集中,打出仙霓社牌子,在东方书场演出中午场,俚又来帮伲吹笛,两头甩。当时俚因生活飘泊,感到人身无常,染上鸦片瘾,加上又好赌钱,欠了一屁股的债。本来俚两头做,一个人开销是绰绰有余的。一次他偷了钱,跑到麦根里车站(现长宁车站)卧轨自杀。刘传蘅为俚料理后事。如果“仙霓社”不解散,赵金虎或许不会沾上赌博。赵传君原来是不吃鸦片的,“仙霓社”散班后,生活无着落,就染上了鸦片,破罐子破摔。1942年冬天,身无分文的俚,鸦片瘾发作,又加上饥饿,侧毙在绿宝赌场外的马路上。传君原先唱老生,后来改演小生,被誉为顾传介后的第一小生,尤擅官生,是位很有前途的演员,却如此结束俚的人生旅程。后来伲到收尸房去,尸体都寻勿着,变成无人收尸的孤魂野鬼。倘若伲在大新公司继续做下去,赵传君也不会倒毙在街头。当然赵金虎与赵传君的死,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当时日寇侵华,社会动荡,风气混浊,意志薄弱的人就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我呒没吃过鸦片,倒不是因为鸦片对人身体有害,而是因为家里小囡多,要靠我养,家主婆家庭妇女,没有工作,阿姐那里也要我补贴,就这一点收入,如果我吃鸦片,家主婆、小囡、阿姐那能办?我是因为呒没钱,才与鸦片无缘。伲传习所也有好几个人不沾鸦片,保持了艺术青春。
插档演出
“仙霓社”散班后,一段时间各管各,有的日子混得好一点,有的混得差一点。我在平声曲社曲友处当拍先,还被越剧界请去当技导。由朱传茗等人发起,聚集在沪的传字辈兄弟,想再建个小班演戏,他们仍联系东方书场(今工人文化宫),叫我一起去。我问朱传茗,行头怎么办?俚说到外面租借。我当时即对朱说,好,我跟奈一起演,行头由我负责去借。朱拍手连声说:“传鉴,到底是自家人。”我去马力斯一带私人出租戏衣的地方去借,那里比较便宜,到店里去借就要贵许多,有的向曲友临时借用。东方书场主要演出评弹,日夜场说书,伲利用中午、傍晚二三个小时的空暇时间,插档演出、称中场。那里演出生意还不错,市口好,加上有些评弹观众也是昆剧迷,俚笃看仔昆剧再听书,亦蛮乐胃。演员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经常变化剧目,观众也还不少。
当时演《武十回》,华传浩饰武大郎,汪传钤饰武松,第一出是(打虎),由华排戏。别看台上汪传钤意气奋发,英俊武勇,华传浩委琐卑昧,丑陋愚民,台下两人却换了一个位置,华神气活现,颐指气使,汪却不好出头,平静少言。华对汪指手划脚,说他打虎动作太慢,汪勿开心,差点吵起来。华这个人真是本性难改。华传浩演《武十回》,到后来一个星期只肯演二场,星期六的夜场星期天的日场,其他时间不肯演出这戏。有一天王传蕖排戏,让华在星期六日场演《武十回》,华大衣一甩走人,只好改戏。汪传钤演戏素来认真,勿偷工减料。就拿《雅观楼》来说,汪传钤是从京剧名武生张翼鹏那里学来的。原来昆班演的路子是由京剧名小生蒋砚香教的,主角李存孝由顾传介、周传瑛饰,小生应工,武戏文演。后来改演张翼鹏的戏路,武生应工,李存孝由汪传钤主演,增设许多武打动作。如耍令旗、打出手,演出后观众反应很好。
伲在“仙霓社”时期,去游乐场演出此较多,有大世界、新世界、大新公司、小世界、大千世界、福安公司,永安、先施两个公司没有唱过,那里主要演广东粤剧及潮州戏。其他剧场有笑舞台、徐园(周信芳经常到徐园来看戏)、大中华剧场(在四马路转角处,今上海旅行社门面)、大罗天剧场(天蟾舞台对面)。说到大罗天,记起一件事。那时北京名角王玉蓉,王瑶卿到上海来演出,王瑶卿偕同陆麟仲(苏州状元陆润庠之子)、翁偶虹来看伲的戏,这天一共售出十二张票,伲照常演出。这个剧场场子小,设备破旧,环境脏差,凳子里有臭虫,观众不愿来看戏。那天我有二出戏,一出《弹词》,一出《斩娥》,我在《斩娥》中演刽子手,昆剧中老生演刽子手不大有。后来翁偶虹在上海小报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郑传鉴演刽子手》。吴江路上有个小剧场伲也演过,名字忘了,已拆除改民房。这个剧场是演沪剧的,伲演中场。
建国初期,在同孚路(今石门路)的同孚大戏院(后改民房)演出,一天日戏演《金印记》,我饰苏秦,陈毅市长来看戏,看后就走,没有现在领导人来看戏那种架势。伲在同孚演了一个月。
跑江湖
“仙霓社”去外码头演出,最先是盛泽,这个地方在上海与苏州之间,属江苏吴县,镇上文化人多,且市面兴旺,所以成为伲下乡的首选对象。以后去的地方有嘉兴、海宁(硖石)、嘉善等地。以前全福班老艺人借行头、主要在嘉兴,那里的戏衣质量好、价格便宜。全福班管衣箱的人是个烂鼻头,大家叫俚塌鼻头。老的江湖班跑码头,要对方四管:管吃、管住、管接、管送。伲只要两管:管住、管接,时间长了形成两句顺口溜:“管住不管吃,管接不管送。”为啥不要管吃?以前吃便宜,饭店里吃包饭,一二元一桌,那家质量好去哪家吃,只要事先订好,俚笃还会送菜上门。如果由剧场包饭,价高质次,吃不好会影响演员的健康。不要管送是因为演出结束,由下家来接,用不着上家送,这样也可节省开支。最后一站演毕,伲自己雇船回去,也可省人家麻烦。
跑码头联系生意,由坐班负责,过去戏班都有一个坐班,伲“仙霓社”时期主要是汪双全。俚的任务就是接生意,总是单独跑码头,接到生意就给戏班捎信,俚每半年排一次线路,到时一家一家落实,戏班在上家码头演出,坐班就前往下家排戏,俗称排下,排下后开单子到戏班,写明几月几日到某地某剧场开演,戏班根椐单子前往演出,很少有变化。有时我自己跑码头接生意,出门时一个背包,带上牙刷、牙膏、毛巾,穿上一件厚的衣服(冬天是棉大衣),经常乘夜船,天一亮到目的地。人虽比较辛苦,但接生意后,心里是蛮高兴的。夜里乘船不大安全,强盗抡是常有的事,我将钱塞在袜子里,不大容易被发现。我接的都是大镇上的剧场。坐班只什么生意都接,乡村的祠堂、谷场的演出也接,也有老爷戏和庙会戏。老爷戏,即神仙老爷的生日,当地人祭祀演戏,如二月十九(农历)的观音圣诞,九月初九(农历)的九皇大帝圣诞。演出的剧目中,有一二出戏要与神仙老爷搭点界。庙会戏,即庙会演戏,过去每个市镇都规定某月某日为庙会日,如三月初三(农历)的清明庙会,三月二十三日(农历)的天妃庙会、四月初八(农历)的俗佛节庙会等。庙会戏演出范周较广,但要与庙会节庆气氛相吻合。老爷戏与庙会戏,有时在广场演出,多以做功,或打翻筋斗的剧目为主,唱曲尽可能要少,因为广场地方大人多,声音嘈杂,演员在台上拼命喊,台下也听不清伊在唱点啥,过去又没有麦克风(扩音器)。
跑马头通常要包三只船,如果下家日程紧,要先开一只船,比方今日在松江做,明日到嘉兴演,全体人马待演出结束动身去嘉兴,路上要十来个小时,如果逆风逆水,行船更慢第二天赶到嘉兴,倘嘉兴要演日场,往往装台、化装来不及,就要影响开戏。为避免误台,安排一只船先开,船上装有部份行头,上家没有戏的或巳经演好戏的演员,带上几个乐师先乘船赶去,一到那里马上装台,万一后面两只船来勿及赶到,伊拉可以先开演起来。
江湖演出,头出戏必是跳加官,当演员展示“吉祥如意”、“金玉满堂”、“恭喜发财”、“五子登科”等条幅时,台下就有人将红包甩到台上来,检场的人见红包就喊:“鸿运来哉!”加官由净扮,戴红翅帽,穿红袍,在台上跳来跳去,由检场将红包拾起交给他。最后一出戏叫《打金榜》,这是送客戏,由老生老旦主演穿官袍,戏中唱曲文,是从各个剧目中摘取的吉祥语唱段,较多的有《百顺记》中的(召登〉(荣归),《儿孙福》中的(福圆)以及《仙聚》等。
码头上演出,经常有点戏,由观众点他们所要看的戏,当然要另外出钞票,多少不论,通常小本戏贵一点,折子戏便宜。如果遇到掼派头的观众,伲也不拒绝。
跑码头演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还有班规、习俗等,比如:接脚戏。如伲十七日上海演出,十九日要到嘉兴登台,十八日途经枫泾,码头上要伲临时演一场,伲正好又有时间,同意演出,这就叫接脚戏。
翻台戏。过去下乡演戏,日戏多在广场草台,夜戏转到镇上剧场,这就叫翻台戏。
曲友会唱,俗称爬台。一出戏以曲友唱主角,艺人当配角,俗叫串龙。
曲友出钱请艺人合演,俗叫三行头。
伲戏班后台有个规矩,演员吵架,不论谁是谁非,都要到戏祖(老郎神)神像前请罪。
地方上火灾演谢火神戏,俗称白袍戏。跳加官平时加官穿红袍,演白袍戏改穿白袍。
菱湖、南浔、双桥一带盛行养蚕,养蚕前要演蚕花戏,演三台白戏,即带孝的戏,因为蚕丝是白的。剧目有《蝴蝶梦》等。看仔三台白戏就开始养蚕。对养蚕人来说,演蚕花戏是吉利的。其程序是:〔将军令〕闹台开场,跳加官〈有头跳——加官,二跳——财神,三跳——报台〉,正戏,送客戏(《打金榜》)。正戏中必有一至二出大花脸戏,演花脸戏前,加官也须出来跳一下,据说是跳掉邪气。通常演《刀会》、《训子》、《北钱》等。《刀会》与《训子》两出戏原来规定不可连演,农民看戏喜欢闹猛,经常要伲连演。
 范海龙新作展
范海龙新作展 崔明涛
崔明涛 “画水者”李
“画水者”李 “EXIN亚洲实
“EXIN亚洲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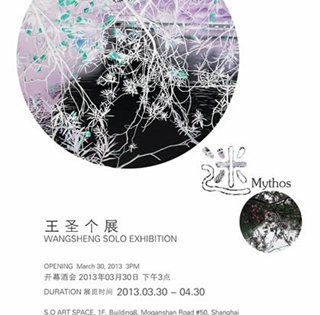 “迷Mythos”
“迷Mythos”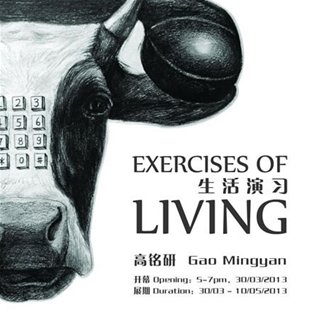 “生活演习”
“生活演习” “中国娇子”
“中国娇子” 传世美谈
传世美谈  历尽沧桑
历尽沧桑